
【王子今】孔鲋的文化立场
孔子八世孙孔鲋是秦代文化闻人。实现统一之后的秦帝国任用了一些儒生多方面参与文化咨询,而孔鲋没有进入这一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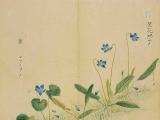
【袁晓聪】《诗经》中的玉
《诗经》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文化经典。诚如宗白华所言:“《诗经》中的诗……它们不但是中国文化遗产里的宝贝,而且也是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的思想感情全面的、极生动的具体的反映。”(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文化的载体,《诗经》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宗周时代的玉礼风貌。

【姜义华】以人为主体: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本质特征
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比较它和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包括那些早已中断的古老文明,就知识体系而言,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特质值得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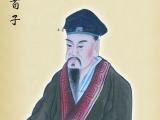
【强中华 林桂榛等】荀子“欲不待可得,求者从所可”章何解?
荀子“欲不待可得,求者从所可”章何解

【陈永跃】吴越文化的几个问题
对于一地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及流衍,必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人群。故历代史家早已将有关问题以普通和专业方式诏告天下。常识常以简洁明了而言,专业是以特殊方法而论。关于吴越文化的常识亦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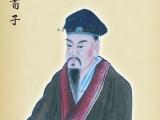
【林桂榛 强中华等】荀子《天论》“错人而思天”错字何义?何种天人观?
张申府一再强调天文、音乐、科学、逻辑、群分,前二者与荀子很相似。

【余东海】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我见——与田辰山先生商榷
田辰山先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的底层逻辑》一文,是某友去年3月函我而让我点评的。东海大不以为然,略予批判。而今此文早已公开发表于《文化软实力》等处,网上多处可以搜到,已没有保密的必要。故将当时的批语公开。是非曲直,公诸天下。功我罪我,任之而已。

【李华】“至善道”与“为真儒” ——从孟子思想流布看秦汉文化选择与价值重构
通过对历经百家争鸣、辩难吸收、秦火之祸而流传至秦汉的三代遗存及“轴心时代”智慧的搜集、选择与承继,汉代最终确立起适用于统一局面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一文化重建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儒学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形式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主流学术思想

【林桂榛、强中华、刘思禾等】关于荀子“性朴”论的微信讨论(三)
心可向善,也可向恶。

台湾「统派猛将」王晓波生前撰文:下辈子一定要做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
岛内“统派”标志性人物、“老保钓人”、“中国统一联盟”(现转型为“统一联盟党”)前副主席王晓波不幸病逝,享年77岁。王晓波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两岸友人纷纷致哀,称其去世“让祖国统一大业蒙受重大损失!” 特别编发王晓波教授生前所撰两文,以表达深切悼念之意。

【吴钩】因为写了一篇不说人话的“高考作文”,他成了落榜生
北宋嘉祐二年正月,万物生发的初春时节,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何善蒙】《春秋繁露》论“心”
“心”在《春秋繁露》中是一个使用极其频繁的观念,共出现133次。对于董仲舒思想系统的建构,心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朱志奇】《尚书》中的治水精神与水利文明
《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代表着最早的中国历史。《尚书》通过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重大历史事件的诰语、誓词等,记录了三代历史更迭、社会经济结构演变,是记载中国上古史最重要的文献。《尚书》叙事自尧舜至夏商周,跨越2000余年,是西周至战国时期人们追述华夏历史的珍贵史料汇编,其中《尧典》《皋陶···

【李山】《诗经》草木谈
离自然的远近,取决于心。今人离自然远,每当春暖花开,面对眼前的青草杂花,看着欢喜,可就是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这不就是心与自然离得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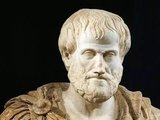
【阿格尼斯·卡拉德】我们应该清除亚里士多德吗?
他为奴隶制辩护,反对人人平等的观念,但他不是敌人。

【万百安】谁在清除亚里士多德?
阿格尼斯·卡拉德的“我们应该清除(cancel)[1]亚里士多德吗?”似乎是为亚里士多德继续作为经典作家进行勇敢的辩护。但是,究竟是谁要将他踢出去呢?

【阿格尼斯·卡拉德】不发表就滚蛋
本文是作者公共哲学专栏的系列文章之一。

【张瀚文】原野的呼唤——读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驺虞》
不去涉足,就很难体验原野的神秘。近读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驺虞》,那里是一片醒着的原野。驺虞所到处,他内心的真诚与自然的祥和交融。虽然风景在纸上,但呦呦鹿鸣,已然在耳在心。

【梁涛】统合孟荀:儒学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儒学研究较多受到港台新儒家的影响,而港台新儒家恰恰是尊孟抑荀,继承并延续了韩愈、朱熹等人的道统观。

【李凯】周代制礼作乐并非一蹴而就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发端于经济领域的铁器牛耕,其对上层建筑带来深刻影响,最终迎来了大一统的秦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