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斯塔夫·琼森】知识分子的背叛
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是法国犹太哲学家、作家,曾在法国索邦大学学习历史。他阐述知识分子和权力的致命结合的经典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本身就是个悖论。

【弗兰克·菲雷迪】历史的报复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刚刚过去两周之后,人们突然痛苦地意识到冷战的结束毕竟并没有标志着永久和平时代的开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俄罗斯的黑暗之心
从政治上说,东欧的悲剧来自这样的事实,其安全最终取决于俄国发生的事。这里的政治合法性不是通过普通的民主实践产生而是通过国内尤其是国外制造的哭喊声产生的。普京已经炮制了好几次自由选举闹剧;他自己觉得好玩儿,但肯定也已经有些厌烦了。

【特里斯坦·泰勒】自我的恶魔
本文作者认为,有意义地定义“罪恶”中存在一些问题。

【约瑟夫·爱波斯坦】古代文人:无可匹敌的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显然成功地做到这些,《希腊罗马名人传》在他写完2000多年后仍然持续吸引充满热情的读者,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他的文学技能,也归功于他的和蔼可亲与迷人魅力。结果,这位孜孜不倦描写人物习性的散文肖像画家本人却意外成了魅力无穷,无可匹敌的名人。

【西奥多・达林普尔】蒙田的人性
最伟大的随笔作家警告我们不要有思想傲慢---同时也以享受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为乐趣。

【马丁·弗格森·史密斯】流行病、瘟疫和哲学:从古至今的道德教训
在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吞噬了百万人的性命,破坏了繁荣国家的经济和数十亿人的生活,制造了很多的恐慌之时,回顾一下古代,看看希腊罗马时期两大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哲学体系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能提供哪些道德指南,或许是非常有意思的。

【莫妮卡・克劳斯卡・斯坦贝克;列尔・卡曼森】来自世界各地的观点
学界哲学真的能够明白我们相互依存的世界,但是只有在真正多元化后才能带来转变。

【约瑟夫·爱波斯坦】永远也不可能发表的毕业典礼演讲
最后,好的大学教育说服任何获得这种教育的人在毕业时相信,自己还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马拉·范·德·卢特】为悲观主义辩护
悲观主义传达的信息是,这也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它值得在我们的语言和共同体验中拥有一个地位;闭上眼睛不看生活中的另一面,那更黑暗、更可怕的一面是不公正的,永远也不公正。这也是悲观主义伦理学的慈爱含义,它未必与乐观主义冲突,但应该作为必要的伙伴和补充与其肩并肩存在。

【彼得·吉布尔】浪漫爱情哲学
本文作者认为,哲学就像爱情,是有着多样精彩的玩意儿。

【尼古拉斯·怀特克尔】独处的权利
本文探讨现代世界的核心假设——独处的需要是人类生活的必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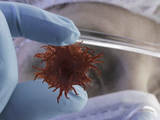
【温迪·沃鲁森】兜售希望
廉价、空洞和毫无意义的东西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最隐蔽的部分。身体健康之时,我根本感受不到这一点。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后现代主义世界末日的预兆
生命本就苦短,文明人将自己的才智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费解。——威廉·萨姆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n),《月亮与六便士》

【丹·泰勒】斯宾诺莎与心灵的麻烦
本文显示甚至伟大的哲学家也会感到心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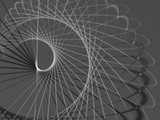
【大卫·荷兰德】故事对观点: 在哲理小说中发现个性
本文认为小说就是要打破沉默。

【威廉·德莱塞维茨】与生俱来的权利
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群体来说,健康的身份认同都不是死板的、无法更改的,而是创造性的、不断变化的。这就是进步。这就是解放。

【艾米丽·托马斯】哲学家-历史学家的反叛:乔纳森·李采访记
本文是艾米丽·托马斯(Emily Thomas)对撰写了颠覆性哲学史的乔纳森·李(Jonathan Rée)的采访。

【阿曼达·布莱恩特】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
这问题,连哲学家们也说不清楚。

【马蒂亚什·莫拉维克 彼得·韦斯特】为合写哲学论文点赞
不过,虽然合著有这些看似明显的好处(不光是哲学几乎任何别的学科也如此),在当今哲学研究的著作中,合著作品仍然是少数。我们认为这是怪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