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荷兰德】故事对观点: 在哲理小说中发现个性
故事对观点:在哲理小说中发现个性
作者:大卫·荷兰德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本文认为小说就是要打破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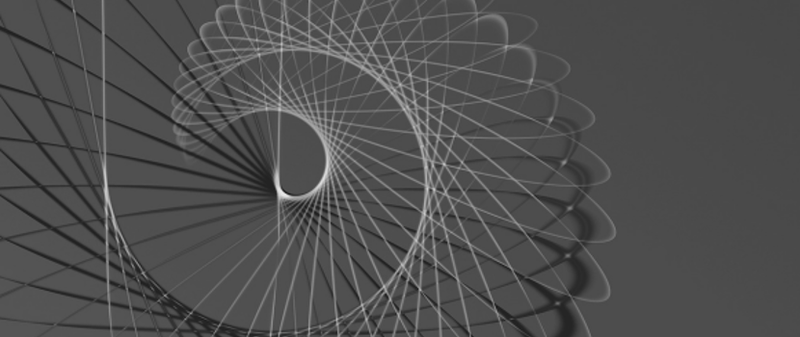
一、宇宙路径
曼哈顿时尚和繁华的上西区有一座令人好奇的建筑被称为罗斯地球和空间中心——巨大的玻璃立方体,里面有太阳系行星的庞大模型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飘浮在空中。作为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该场所因为其世界一流的海登天文馆(Hayden Planetarium)而闻名天下,但是,在其给心灵带来巨大冲击的装置中,我最喜欢的是所谓的“宇宙路径”。130亿年的宇宙历史以360英尺长的踪迹旋转向下呈现在你的面前。其顶点代表大爆炸——虚无变成一切的时刻——然后一步步往下走,穿越千万年的宇宙演化史来到时空环境中的当今时刻。
沿着铁道线悬挂的海报揭示了你的旅程:这里第一个氢原子诞生;这里,数百万年之后,首批恒星的大爆炸而存在,将更重的元素抛向虚空;这里,数十亿年后,第一批行星从火中诞生,进入不稳定的运行轨道。不断往下走,经过数百个台阶之后,你最终来到螺旋的底部,这里你看到展出了一个小玻璃盒——在白色棉花画布上——是人的一根头发。在这根头发下面写着:这根头发的宽度代表着人类来到这里有多久了。
这是很谦卑的姿态,也是——对拥有我这样立场的人来说——也令人恐怖。我们对待人类头发的宽度就好像它十分重要似的,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人类物种来到这个世界,在宇宙眨一下眼睛之前它恐将消失。施虐的疫情、食物的短缺、水的缺乏、从太空都可看见的大火、大范围的洪水泛滥、大面积的干旱。。。人类似乎以看得见的惊人速度奔向自己的终点,就像那些快速飞驰的电影卷轴样的花朵绽放(或者更合适的说法,就像在树枝上枯萎的花朵)。但是,当然,我们必须生产制造一种稳定性和永恒性的幻觉——为了生活。这里没有什么可丢人的;从体验中获得意义是硬连接的人类特征。反对这一点就如同要求蜜蜂停止传授花粉般荒谬。
但是,从小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迫切渴望——或需要——将人类物种的规范和习俗与更大的东西联系起来,感受到我们属于某种永恒真理或宇宙真理。否则,在我看来,我们的整个信仰体系及其指导下的生活在微小的人类真空中展开,虽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从宇宙视角看,人类稍纵即逝的存在其实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因此,宇宙路径底端的人类头发就像那根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the Sword of Damocles)的头发一样,一旦有一天它突然断裂,我们的短暂统治将悄无声息地完结。
为了产生真正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获得宇宙真理,获得上帝一样的视角。因此,至少这一直是我不顾一切迫切追求的微积分。
本文是以自己的方式写成的有关小说创作的文章,有关我为何当作家,小说如何在真实的意义上让我免予落入绝望的深渊。但是,或许非常明显的是,我是从非常怪异的角度走近小说的,比如我从来不想“讲故事”,这是大部分作家小时候都常做之事。在成长过程中,我没有想象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作家。虽然我在大学读本科时学的文学,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这些东西。
虽然哲学可能漂亮地描述我们人类囚笼的形状和维度,但只有艺术能够敲响囚笼的栅栏,使其嘎嘎作响。
阅读简·奥斯汀(Jane Austen)、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我感受到的是人们对19世纪装饰石墙的布鲁克林褐石外墙(Brooklyn brownstones)的那种欣赏:我知道我站在漂亮的巴洛克艺术品面前,但对于我每天都感受到的存在恐惧,需要对付的,它们并不能让我感受到相关意义。它们似乎也没有与当今生活中令人困惑的速度和旷达有多大瓜葛。
我的确发现交流时空大问题的尝试的地方不是文学而是哲学。鉴于我对人类系统的价值观和可靠性的怀疑,我曾经希望——就像很多学习哲学的年轻人一样——弄清楚我应该如何生活。对我来说,哲学的好处就在于它为我提供了更牢固的基础,我可以在其上摇晃。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特别具有指导作用,他向哲学引入了这样的观念:你不能在不谈论主体时谈论世界,而这个世界已经被主体过滤了的。这限制了我们对概念框架的形状和形式的本能性认识。在谈论真理和意义时,我们在讨论对我们或人类来说的真理和意义。康德完美地表达出了我的难题,但对我来说,显然是哲学进步基石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确认而已,即我永远不可能是整体。
奥地利哲学家(或许是我心中最大的英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经说过“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与此相关,“如果狮子会说话,你也未必听得懂。”毕竟,狮子的世界与我的世界大相径庭;其语言可能随着狮子世界的必要性而增长,而不是满足人类世界的需要。维特根斯坦谈论语言的方式揭示出哲学经典中形成的这么多看似深刻的命题其实都是废话。维特根斯坦说,哲学是当我们痴迷于语言不能自拔时发生之事。那是当我们试图让语言做它不能做的事,说比它能说的话更大的话时所发生之事。
维特根斯坦治愈了我的毛病,让我重新对哲学燃起希望,相信哲学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本来可能错过的宏大永恒真理。我可能拥有的幼稚信念---通过思想或意志---像上帝一样认识世界必然死掉了,留下了一种虚空需要用思想之外的东西来填充。(感谢上帝,因为我不是聪明人,我的智慧无论多寡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找到一种方式将每个问题转变成为本文试图表达的那种问题)我一厢情愿的思考或许得到治愈,但我仍然无法应对这个事实,即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宇宙真理”。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不错,但它也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办法逃脱的牢笼。
维特根斯坦的著名建议是“在不能说话的地方,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我迫切希望得到的客观性(或者上帝真理)似乎不仅仅是捉摸不定的;到现在为止它似乎在我们的牢笼之外,我们甚至不能开始谈论它。维特根斯坦说,别说话;再也没有更多需要知道的东西了。
但是,虽然我在内心深处明白维特根斯坦是正确的,我仍然没有办法屈服于表达真理的追求,这个真理是超出他确定的沉默之外的。上帝就存在于那些沉默空间的某个地方,我想对他们尖叫血腥谋杀。我发现的--至少部分通过阅读之前从来不了解但确实存在的小说---作为研究19世纪小说的学生---是这个内容,即虽然哲学可能漂亮地描述人类囚笼的形状和维度,但只有艺术能够敲打囚笼的栅栏,使其嘎嘎作响。
在后现代小说家之一实验文体作者罗伯特·库佛(Robert Coover)、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和英国著名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作品风格独树一帜,混合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哥特式及黑暗系童话,想象奇异诡谲,语言瑰丽璀璨,充满戏仿的狂欢——译注)的小说中,我发现了一种叙述破裂,它很少与故事的实际内容相关,更多是抵抗人类系统的形式。
这场神灵顿悟出现在我读本科时的最后一年,我选了一门当时还不知名的作家里克•穆迪(Rick Moody)的课,他是实验派文学或后现代文学的粉丝——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的小说阅读经验一直局限在大学生的经典文本和逃避主义的科幻小说(后者帮助我度过痛苦不堪的青少年时期)。但是,我在通过穆迪接触到的文本中发现一种并非和讲故事结合起来的意义。在罗伯特·库佛、唐纳德·巴塞尔姆、安吉拉·卡特的小说中,我发现了一种叙述破裂或者不稳定性,它们与故事的实际内容没有多大关系,更多是一种抵抗人类系统的形式。
实际上,那时的一篇小说,即罗伯特·库佛的“照看小孩的人”20年后仍然留在我的教学大纲中。我喜欢讲给学生听它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那是一篇冷小说,里面找不到可验证的角色,“情节”也荒谬可笑:一帮中毒似地痴迷于男子汉气质的男生都迷恋上了一个“照看小孩的人”。这篇小说对我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意义就是它自我吞噬的结构感觉很像我自己的大脑模式。每次“一条真理”来到“照看小孩的人”,马上就被另一个不同的真理和不同的现实替换掉了。没有核心的或客观的权威来源。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在我看来似乎就像我在经历的一场斗争,要找到或表达某种“普遍可证实的真理”。它似乎被直接指向维特根斯坦警告我要反对的试图渗透进的沉默空间。
“照看小孩的人”的量子结构并不类似“真实生活”的组织或者逻辑。那是它能够给我带来令人担忧的影响的原因,这个影响与其说与故事讲述的内容有关倒不如说与它的行为方式有关。它让我觉得(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上帝般的大小”。
我不是说库佛是宗教作家。他是后现代骗子,他喜欢玩游戏,把读者的期待搞得一团糟。但是,他的方法打开了一扇门,可让人进入很多房间:到贝克特(Beckett)、到博尔赫斯(Borges)、到加拿大女诗人、翻译家、小说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意大利短篇小说家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到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和巴西女小说家克拉丽瑟‧李丝贝朵(Clarice Lispector)。文学中我爱的一切都在敲打我们概念框架的边缘,迫不及待地试图把若干课程大纲扔进我们无法谈论的那个空间。
跟随我到此处的读者或许高兴地知道我们已经来到本文中我要讨论小说写作的部分,更具体地说,有关某些作家和读者如何以及为什么偏向——或者甚至需要——非传统小说和野心勃勃的小说。如果你怀疑系统,如果你觉得你阅读的几乎每本小说都在某种程度上都错过了要点,如果小说在你看来没有能处理宇宙路径的人类头发所暗示的问题,那么你开始寻求一种有能力嚎叫的小说。(我不知不觉地想到了牙买加最伟大的音乐家和民族英雄里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吹嘘:我到此地不是来乞求的而是来征服的。)
二、普遍性战胜个性:若干例子
我承认自己在文学中寻找的东西类似于大部分人寻找的东西。我并没有试图给他人开处方,应该阅读什么作品,也没有贬低大部分人最喜爱的作品的意思。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惊悚小说、大幻想系列小说。。。我很高兴人们阅读这些东西,并从中获得快乐和安慰。它们或许不能满足我作为读者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但简奥斯汀和狄更斯的小说同样也不能。我并不是说,简奥斯汀不是伟大作家,她当然是伟大作家,但她的小说是从我一直在描述的内心深处的囚笼内部写出的。她并不担心“世界本来样子”的客观真理或不可知性。她为什么会这样?她实际感兴趣的是人的生活,而我似乎感兴趣的是更普遍的人性是什么,我们有限的潜能如何产生了矩阵一般的幻觉。如果这里真的有人拥有扭曲的性格和视角,亲爱的读者啊,那就是本尊(C’est moi)!
本文不是谈论伟大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篇谈论像我这样对系统感到怀疑,且有可能滑入危险的虚无主义深渊风险的家伙如何通过文本获得救赎的文章,那些文本暗示还有比我们直接认识到的东西更大的意义。
但是,这样的文本看起来如何?它们的行为方式如何?很容易说(我常常这样说)“若看到了,我能认出来”,但这种说法虽然真实却也蹩脚得很,难以说服他人。在下文中,我希望提供若干作品为例子来做一番说明。它们似乎“拒绝提供服务”,反而嚎叫着要打破维特根斯坦的沉默。该清单只是提供若干典型而非穷尽所有;这种类型的小说的外表并没有一套前提条件,它飘浮在当今大部分小说排行榜最畅销作品的小说写作方法之上,这种方法是身份认同驱动的,且吻合社会规范的。
《血色子午线》
在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代表作《血色子午线》的如下魔咒段落中,我感受到了神圣的、无利益纠葛的刺激:
那个夜晚他们骑马经过一个电场和荒原,那里柔和的蓝色火焰的怪异形状飘拂在马的装饰金属上,车轮在火圈中翻滚,淡蓝色光线的微小形状逐渐停留在马耳朵和人的胡子上。整个夜晚,片状闪电没有源头地振动向西超越午夜的雷暴云,让远处的沙漠变成蓝色的白天。突然显现的天际线上山脉荒凉光秃秃黑黢黢青灰色就像一片外星人的土地,其真实的地质学构成不是石头而是恐惧。雷声从西南方向朝上走,闪电一下子照亮周围的沙漠,蓝色和荒凉,庞大的叮当响的前沿被勒令赶出绝对安静的夜晚,就像某个魔鬼王国鼓起勇气或者掉换生灵者的土地有一天将离开它们既没有痕迹也没有烟雾,除了搅坏噩梦之外没有任何破坏。
麦卡锡这里(和几乎任何地方)使用了无连词并列; 意合连接的手法,从句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快速累积起来的一种风格。他回避了定义相反风格---从句的使用; 从属关系形合手段的从属连词。麦卡锡没有说,“在骑马经过一个电场和荒原的时候,这些人注意到西边的天空中出现了闪电雷暴。”相反,使用并列连词“和”,他将行动和描述疯狂无情地胡乱堆砌起来。(有时候在我大声朗读他的作品时,甚至担忧我可能偶尔招徕恶魔)。
麦卡锡的无情使用并列连词和他冗长的节奏性花彩有某些深刻的根源。比如,这是通常被称为创世记中摩西一书的开头(黑体是作者添加的)。
创世记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这里,我们看到同样没有逗号,并列连词频繁出现的意合连接。麦卡锡能使用的理由之一似乎是在书页上从头创造一个世界,他在呼应宣称记录了世界从头开始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文本。
如果这里真的有人拥有扭曲的性格和视角,亲爱的读者啊,那就是本尊(C’est moi)!
麦卡锡的著作谈论了很多东西,其中之一是宇宙对人无可争议的敌意。《血色子午线》一次次探讨了可怕的暴力,然后回归骑马在有裂隙的沙漠风景穿梭的无意义跋涉。使用《旧约全书》的风格传递出与《创世记》旨在传达的信息有时候正好相反的信息。麦卡锡夸耀了我们的宗教神话,同时暗示完全的不充分性和不正确性。它创造出全球性的不和谐音,或许就是为什么我在阅读他的句子时,即便缺乏所有背景也能感受到刺骨的寒意。
将这两种不大可能的东西集中在一起造成的感觉比麦卡锡实际说的任何话语的威力都要强大得多。他的深刻且不和谐音的震动进入维特根斯坦警告我们试图穿透的那些空间。但是,当然,麦卡锡的超级男性(常常野蛮残酷的)写作并非对这种效果的美学和哲学垄断。他不是唯一认识到宇宙路径尽头那根头发的人。
《红色自传》
在安妮·卡森(Anne Carson)自成一格的“诗体小说”《红色自传》是从形式和语言上模仿经典的作品——据说是对不知名的古希腊诗人斯太希胡罗斯(Stesichoros)写的故事进行的怪异的重新概念化,记录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akles)杀死住在红岛巨人革律翁(Geryon)的故事,这个恶魔总是由他的红色狗和“相应的红色微风”伴随。
小说十分怪异的前部包括一篇文章辨认出形容词是小说和史诗之间的关键,还有一个邀请你解读希腊诸神对待斯太希胡罗斯写作态度的流程图。最引人注目的是,早期附录中还有斯太希胡罗斯的原始文本的一系列片段,这是作为希腊经典学者的卡森本人翻译出来的。这里有一篇:
有关革律翁的已知信息
他喜欢闪电他住在岛上他母亲是流到海里的河神宁芙(Nymph)
他的父亲是切割金子的工具古代学者说斯太希胡罗斯说革律翁有六只手六只脚和翅膀
他是红色的他的怪异奶牛激怒了嫉妒的赫拉克勒斯(Herakles)前来为了他的牛杀死了他
还有狗。
最终,卡森下来进入小说本身,她想象了斯太希胡罗斯的革律翁的现代版本,一个男孩在加拿大的某个地方长大,有个性虐待狂的哥哥和爱他却无能为力的母亲。卡森的革律翁是某个长着翅膀的红色魔鬼,同时又是艺术家那样大脾气的青少年,最终爱上了一个名叫赫拉克勒斯的年轻人。他既是小说的主体(因而拥有自由意志)同时是不变史诗中的死亡-对象(因而注定永远被毁灭)。最奇怪的部分是那个革律翁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头脑中时常萦绕着史诗,看到斯太希胡罗斯对他的死亡描述,看到他被空运出去。
在文本的初期——上文摘录的部分中删去了大约25页——革律翁陪伴他母亲去参加小学校的家长会,在那里老师分享了革律翁的作品(你在这里看到的):
观念
有关革律翁的全部已知事实革律翁是魔鬼,他的一切都是红色的。革律翁住在大西洋一个名叫红色场所的小岛上。革律翁的母亲是一条流入大海的河流(红色快乐河),革律翁的父亲是金子。有人说革律翁有六只手六只脚,有人说有翅膀。革律翁是红色,他的怪牛也是红色的。赫拉克勒斯有一天杀死革律翁,俘获了牛。
(老师继续问,“他是否描写了大团圆的结局?”)
我故意选了最少微妙含义的结构的例子,这些结构经常出现并且搅动其强大的逆流:古代和现代,单调和怪异,死的知识和幸福的无知;活物的死亡和文学人物的不朽。
这本书的文笔很好(卡森是描述“白色空间”的大师,虽然她的缩微章节往往只有不足五分钟的体验,章节之间往往要过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维特根斯坦式的沉默被嵌入在其著作的结构中),但写作技术本身并不能构成一本引发如此激烈反应的书。在暗示时间已经是写出和完成的时候,AND总在不断展开而且受制于我们的决策。卡森创造了某种新的、令人惊讶的东西,一个在情节结构上谐调却在意义上不协调的文本。它的振动就像刚刚苏醒的火山低沉而持续的隆隆声延伸到沉默之中。
《霸凌诗学》
很难找到一个比斯坦利·埃尔金(Stanley Elkin)的精彩小说《霸凌诗学》的“推挤恶霸”(Push the Bully)更加坚定不移地决心打破自己牢笼的叙述者了。埃尔金使用了亚里士多德形式的“诗学”这个词来表示艺术或事物的本质。小说的开头如下:
我是推挤恶霸(Push the Bully),我讨厌的是新孩子和女孩子,不管是笨孩子还是聪明孩子,富裕孩子还是穷孩子,或者戴眼镜的孩子,谈论可笑的事情、炫耀,巡逻兵和聪明人和传递铅笔和给植物浇水的孩子——尤其是瘸子。我喜欢谁也不爱我。
有一次我在推挤这个红头发孩子(我是推挤者,不是打人者也不是真身演唱的歌手,边缘暴力的攻击者,我讨厌真正的暴力)他的母亲把他的头推向窗外,喊叫了一些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推挤”,她喊叫“你,推挤。你选择他是因为你希望你有他那样的红色头发。”这是真的,我的确希望拥有他的红头发。我希望我个子高或身体胖或瘦。我希望长一双颜色不同的眼珠,拥有不同的手,还有一位在超市工作的母亲。我希望我是男人,是个小男孩和唱诗班的姑娘。我是个宗教皈依者,内心装着整个世界的波士顿黑人。我没完没了地觊觎和装箱。(你知道什么让我哭泣吗?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那真漂亮。)
小说的结尾是“邻近社区上帝”的推挤恶霸与学校里的新孩子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一场打架。这孩子是终极做好事者,似乎决心要清除推挤恶霸在生活中制造的所有错误。一方面,这是非常容易懂的故事,两个相互讨厌对方的小孩最终肯定要打一架。另一方面,这是《失乐园》中路西法(Lucifer宗教传说的人物,基督教中的堕落天使,是堕落前的撒旦(Satan)——译注)做出的决定:“宁在地狱为王也不肯在天堂里俯首称臣。”
在小说的最后场景中,恶霸普希和约翰·威廉姆斯最终在校园柏油路上狭路相逢,普希说出了这样的话,“任性的家伙,竟敢连我也不放过。恶霸普希讨厌你。”他在对着约翰威·廉姆斯说话,当然,他似乎也在对上帝说,根本无法在他虐待狂式残忍地创造出来的人身上发现上帝自己的完美性。
在我与学生分享这本小说的时候,不得不带领他们越过最初的观察“没有任何霸凌者真的会这样讲话。”当然,这部分的摩擦源自明显的几乎像数学公理一样的常识。任何霸凌者都不会真的这样讲话,但普希就这样说了。他变成了你迫不及待要捧场的人,成了人类抵抗压迫性的神圣一致性的象征。他不能被禁声。
《迷宫》
本文开头谈论的是我从哲学转向小说的旅程。在此旅程的最重要部分陪伴我的作家是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他的著名小说集《迷宫》中的故事就像数学公式一样被完美地制造出来。小说采用时间、无限性、重复的观点,驱动人的灵魂直接到达能够容纳的边界。小说集中的每个故事都挑战了我们有关文学是什么和能够成为什么的假设。在此过程中,博尔赫斯拆解了个人多么特别,自我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
在《环形废墟》中,一个人试图梦想另一个人的存在,他成功了,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发现自己也被人做梦了。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博尔赫斯想象了一个人在一次坠马事故后获得了超凡的记忆力,他能一字不落地记得看见和点滴不漏地复述经历过的任何事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记忆不能做到这样,并不能给自我提供安全的藏身所。但是,《迷宫》中对我来说或许意味着最多的一篇小说是最后的一个寓言故事,题目是“博尔赫斯和我”,开始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人,一个名叫博尔赫斯的人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穿行,偶尔停下来观看前厅的弧形拱门或者大门的格子形图案,现在几乎是机械地观看了。我是通过邮件认识博尔赫斯的,在教授名单或传记辞典里面看到了他的名字。我喜欢计时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术、咖啡的滋味和史蒂文森(Stevenson)的散文;他和我有这些共同的爱好,却以虚荣的方式将其变成演员的性格特征。
这个小小的寓言拥有一种忏悔的感觉,在系统性地消解作者,将其简化成一套可观察的性格特征。除了这些感知之外,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宣称自己的个性吗?自我是语言和规范维持的幻觉吗?叔本华曾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无限的时间在我出生以前已经过去。在这个时间,我是什么?从形而上学角度看,可能这样回答。“我曾经总是我”;也就是说,所有在那个时间说“我”的人都是“我”。”
“博尔赫斯和我”最后以这样令人胆寒的话结尾: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摆脱他的束缚,从城市郊区的神话传说到时间和无限性游戏,可是现在这些游戏都已经属于博尔赫斯了,我不得不想象其他事物。因此,我的生活变成了逃逸过程,其中我丧失了一切,如今一切都成他的了,或者淹没于遗忘之中。
这一页的文字是我俩哪个写的,我不知道。
博尔赫斯的小说完全不关心当今小说痴迷的任何一种内容。社会正义、交叉性流派理论、个别性、身份认同驱动下的思想和写作中“呆在你的车道上”的本质。这些在博尔赫斯的范式中变得荒谬可笑。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作品似乎显得冷漠、模糊、缺乏相关性。但对于少数读者来说,这是面向虚空的嚎叫,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虚空的存在。
三、令人恐怖的宇宙空间
这四个例子——在经过大量模棱两可之后选出——并没有开始耗尽我尝试在此讨论的反牢笼小说的参数指标。对体系的必要冲击能通过预先假设的无限数量的形式途径或审美途径而出现。一定比例的途径或许有资格成为“实验性小说”,可能令很多读者望而生畏。
在我看来,拒绝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呼吁的这些作品的定义性特征是它们看重神秘性、不和谐性和普遍性而不是解释、和谐和特殊性。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看不见的城市》)就具有神秘性。依据被称为“斐波纳契数列”(the Fibonacci Sequence)的数学结构作为框架,该书塑造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忽必烈汗(Kublai Khan)持续进行的对话。它以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汗帝国众多城市的描述为主架,但实际上是深潜到语言本质的深处和世界认知(不知道)。在我看来,这是纯粹的魔法巫术。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儿童作品中同样存在这种力量路径,比如我记得见过一张早熟的幼儿园小朋友的图画书,这是格罗弗(Grover 芝麻街那么有名的) 讲述的被称为《本书最后的魔鬼》。格罗弗试图说服你不要翻动书页(以便不遭遇那个拥有这个称号的魔鬼),没有意识到他就是那个魔鬼。这当然应该是好玩儿的玄小说玩笑;但它让我感受到刺骨的凉意。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女巫被允许依据如时间一般古老的魔法规则处决阿斯兰(Aslan)。但阿斯兰能够回来,因为他有机会接触比时间更古老的魔法!
在我看来,拒绝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呼吁的这些作品的定义性特征是它们看重神秘性、不和谐性和普遍性而不是解释、和谐和特殊性。(罗伯特·史密斯森(Robert Smithson):“确立神秘而非解释”)这些著作不是来为我们的体系服务的,它们是来征服体系或至少是抗拒体系的。
这就是我想从文学中寻找到的东西。当我阅读(写作)小说时,不是在讲述故事而是试图超越故事,超越地球的宇宙飞船在人类社会上空盘旋的方式。我明白这是多么怪异的痴迷。但是,我在经历文学时不能不了解宇宙途径的宇宙真理。我不能忘记人类世界在整体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头顶。
我是在人性圈子里过生活;我是父亲、丈夫、老师。但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用帕斯卡尔的话说,我这样做“是宇宙的可怕空间把我圈进来了。”在承认这些空间时,仍然存在艺术的可能性,存在生存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大卫·荷兰德(David Hollander),作家,著有小说《神人》(Anthropica)(Animal Riot Press, 2020)和《L.I.E.》(Random House, 2000))。
译自:Stories vs Ideas: Finding Something Deeply Personal in the Philosophical Novel By
https://lithub.com/stories-vs-ideas-finding-something-deeply-personal-in-the-philosophical-novel/
【上一篇】【威廉·德莱塞维茨】与生俱来的权利
【下一篇】【丹·泰勒】斯宾诺莎与心灵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