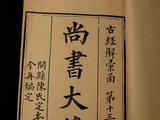
【吳笑非】《書》學肇始
《尚書序》:“鄭作《書論》,依《尚書緯》雲:‘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

【郑红霞】孔子的儒家学说
在中国过去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上,孔子及其儒学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上起了主要的作用;现代意义上孔子是儒家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孔子更为人类社会尤其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张艺瑶】戒骄戒躁
经过了一整个长夏,暑热还未消散,骄阳仍似火,偶尔有一阵微风吹来,浮躁之气便仿佛散去了几分。

【慕朵生】《春秋》天子爵称暨孔子改制考三条
《春秋》天子爵称暨孔子改制考(一)】《春秋》爵三等,天子一等,公侯一等,伯子男一等是也。何三等?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法三光而爵三等,公侯伯是也,以天子乃天之子而天所命故不爵称;夏文者主地,法五精而爵五等,公侯伯子男是也,以天子乃天之子而天所命故亦不爵称。
-53.jpg!cover_160_120)
【吳笑非】禮法二元治理初論
本文是“第一屆經學、經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討會”的稿件,感謝會議諸君賜教,更待方家訂正。

【慕朵生】《春秋》中的“天子”和“人子”
上帝有着重要的政治神学内涵。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王者受命于天”,是为“天子”。盖“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宣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

【慕朵生】《春秋》是全体大用之书
说《春秋》是史书、经书、王书、礼书、刑书、政书、宪书云云,皆是就《春秋》之某一特色和优长而表出其某一体某一用。

【张浩浩】《论语》的诗性品格
孔子曾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论断。那么《论语》作为儒家学派,乃至中华传统的经典之作,也具有鲜明的诗性品格。孔子不仅引述诗歌,还教诗、论诗,活出了高层次的诗境。

【陈嘉许】《周易》里的妲己
象辞说,“夫征不复”意谓“离群丑也”,“妇孕不育”意谓“失其道也”,文王羑里之难,陷入了小人的包围,因为商朝变得无道了。“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同时暗涉妲己品行对纣王的负面影响。

【丁纪】《中庸》首章说
癸卯理学班第二场,毕冉主讲大本达道,我略加评议。评语虽匆遽间出之,似非毫无可味者,因追记并稍完其意如次。

【余东海】做好人不必求好报,做好人必然有好报——因果微论
好报包括物质性、功利性、精神性好报,都是道德的副产品。“君子固穷”不能那样解释。这里的固与“小人穷斯滥矣”的滥相对,是坚固、不动摇的意思。“君子固穷”与孟子“贫贱不能移”近义。

【刘青衢】德教说
人生万事,不学则不能,学则有教,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教有三义:一曰道德之教,一曰知识之教,一曰技能之教。技能之教,如训练工匠之类,重在实践,用以改造世界也;知识之教,如钻研科学之类,重在理论,用以认识世界也;道德之教,如为人处世之类,自有其知见与工夫之为一,用以修己安人也。成人之德,在有道德之教···

【陈嘉许】干支本义一说
古人使用干支纪年月日时,天干就表达了天地之间阴阳五行按照木→火→土→金→水→木→……顺序的循环主导,地支则体现了该天干所处的时空定位,或者说该天干赖以施展的平台情况(此时易学术语称为受生、得地,或受制、不得地,等等)。从而,干支纪时的方法不是随便安排的,而是一套精妙、成熟的理论体系的产物。

【陈嘉许】关于《洪范》五行的一点解读
五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尚书·洪范》被认为是最早明确涉及五行的文献。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在前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有关文本及其意义,聊备一说。
-50.jpg!cover_160_120)
【许石林】有人问:怎么看陈丹青、王朔等等名人骂孔孟儒家?
陈丹青、王朔等嘴上骂儒,但他们为人却不失朴素的正直,其实怀有儒心儒德而不自知,也就是说,陈丹青和王硕身上的“含儒量”不低。这一点,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也说不清。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吳笑非】井田、公田、私田
《公羊傳》: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吳笑非】《孟子字義疏證》非漢學而近時學
《孟子字義疏證》:問:古人之言天理,何謂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於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於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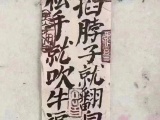
【孔子岛】坐井观天,自欺欺人,仍是中国哲学界教授之绝对主流……
约翰·洛克躺在这附近。你若要问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回答:他是一位满足于小康命运之人。被培养成一位学者,他的学问只服从于真理。对此,你可从他的著作中得知。他的著作还会向你展示关于他的其他事情,较之于墓志铭名不副实的赞词,他的著作更加真实。他的美德,如果有的话,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更不足以让你仿效。

【徐将晓 张宇谦】行夏之时 ——吁请将中国传统历法纳入国家级非遗保护
《晋书·历志》载:“炎帝分八节而始农功,轩辕纪三纲而阐书契,乃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创律吕,大挠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考定气象,建五行,察发敛,起消息,正闰余,述而著之,谓之《调历》。是故历法之作由来尚矣。”
-10.jpg!cover_160_120)
【许石林】雅人深致,岂可多得
书法家刘敏豪兄以诸体字书百联,幸先得拜观,反复品读,真可谓雅人深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