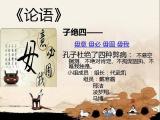
【刘青衢】毋我说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斯乃圣人大圆境界,亦示学者以修己安人之无上心法,垂千万世,不能易其辞也。

【吳笑非】等級制有二,華夷社資之別
荀氏《易》注曰:“尊卑貴賤,衣食有差,謂之理財。”(繫辭下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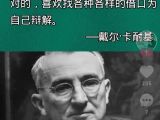
【许石林】卡耐基所有的话,都逃不出孔夫子手掌心
住“坟景房”,古人心理比今人强大。

【慕朵生】“陈桓弑其君”与“孔子作《春秋》”
孔子者,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中心也。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即是以孔子为中心,孔子之前两千五百年——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也,孔子之后两千五百年——有孟荀董何程朱陆王是也。

【许石林】李光耀先生被曲解误传的一句谦辞
李先生谦虚地说:来南洋闯荡创业的华人,基本上都是穷苦华人,无士大夫读书人之家移民,因此,新加坡用了英国人留下的法治,而没有发挥儒士大夫读书人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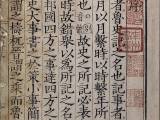
【刘怀岗】王者兴起为何先治郑
凡天下之乱,国家之间相互倾轧,根本在于无王。当周幽王失去天下,平王东迁,天下实质无王,从此开始了列国争夺的局面。春秋经应运而作,当一新王,摄王道以治天下。

【刘洪玮】是人斯人辨
近闻网络以《孟子》是人、斯人爲辩,竝有影印本、排印本截图爲证,登热搜第一。此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章,《语文》课本所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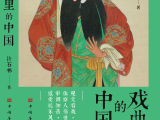
【许石林】文艺作品评比不能“唯出身论”
近些年参加了一些文艺评审评奖,所见评审评奖标准中均特别设“是否原创”一条,即作品、节目属原创则加分。
-16.jpg!cover_160_120)
【许石林】身处精明计较之世,人可贵的恰恰是迂阔
中秋国庆双节,连续值班两天,2日下午居然中了暑。没想到,大夏天几个月没事,过了中秋,中午逛了逛菜市场,逛者脑袋在太阳底下走了走,倒中暑了。

【梅志】蒋庆先生七十寿序
先生遠出周公,姓蔣氏,諱慶,字勿恤,號盤山叟,生於貴州貴陽,後學稱盤山蔣子云。先生年至古稀,初度之辰,時在國慶。中華上下,舉國為歡。後學梅志,遙祝先生:盤山俟聖兮,反袂拭沾。思比江水兮,壽若南山!
-1.jpg!cover_160_120)
【许石林】《水浒传》最动人的是这一段,从前不愿看,现在反复读不够
前日讲座,分享二十四节气之“白露”节气文化。听众对讲座中提到的大雁文化很感兴趣。
-3.jpg!cover_160_120)
【慕朵生】《春秋》之为“王书”三说
《春秋》是史书、经书、政书、礼书、刑书、宪书云云,知之者夥矣。《春秋》之为“王书”,则须作必要的说明,而其要有三

【陈绪平】三代之道:从周公制礼到孔子定经
孔子删定《尚书》,以“二帝三王”为典范。二帝即尧、舜,三王则是大禹、商汤和周文王。孔子把这五位君王的天下治理,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峰,故称之为“圣王”。由圣王之道开创出来的治理秩序,则称之为“王道”秩序。

【崔云飞】《孟子》的“创业垂统”与“创业之君”
孟子最早提出“创业垂统”的说法。孟子说:“昔者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创业垂统的开国君主也被成为“创业之君”。。而“可继”就是“继体守文之君”(或“守文之君”)。此后“创业垂统”“创业”不断出现···
-7.jpg!cover_160_120)
【彭凯平】人际关系质量关乎个人幸福
关于“什么是人类的美好生活”,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对此做出的回应是一项始于1938年的科学探索,迄今已达85年,更迭了三代人,包括最初的724名参与者与他们的1300多名后代。它如今还在继续发展壮大,成为有史以来对人类生活进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深入性纵向研究,也成为心理学史上最长的一项努力揭示美好生活与人类幸福的伟大作品。
-10.jpg!cover_160_120)
【吴笑非】攝政與攝位
《箴膏肓》:“何休曰:‘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隠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箴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隠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且《公羊》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

【慕朵生】论《春秋》亦为“史内传心之要典”而尤能提撕人性之堕落
数千年来,人类文明之丕变于当今之世为甚——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是“陌生人社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带来的则是“虚拟人社会”。这个新型的陌生而又虚拟的世界,与传统的熟悉而又现实的世界,有着重大区别乃至是天壤之别,而此前种种习以为常、视为当然的传统道德伦理规范正在逐渐变得失力失效,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人心人性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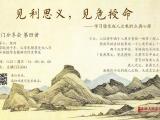
【张艺瑶】见得思义
“见得思义”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篇记录了一些孔子以数字作出归纳的人生戒示,包括我们熟知的“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等,于简明之中见深刻内涵。

【陈明】我的中小学老师
发蒙是好像是1970年,长沙南区的沙湖桥小学。父母都在自来水厂工作,住在南站道坡宿舍。从家里到学校走路大概需要二十来分钟。从坡上下来的拐角有一个小铺子。瓶子罐子里装着梅子、蚕豆、冬瓜糖之类的零食,现在又都复活了,但不再是从前的味道。

【陈明】宝古佬与云山院
“长沙里手湘潭票,湘乡嗯啊做牛叫”,“里手”“做牛叫”都有调侃之意,“票”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褒奖之义。但是,如果湘潭人、湘乡人都属于宝古佬,那么勉强把它解为“勇猛”至少字面上可以成立,古籍就多有“票帅”“票雄”的用法。一直都有办书院的情结,顺义的院子被强拆后有点心灰气冷。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云山院传道受业再续弦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