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jpg!cover_160_120)
【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29.jpg!cover_160_120)
【许辉】北朝时期幽州的儒学与士族
北朝时期是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的时代。他们纷纷建立政权,主动拥抱汉文化并最终走上汉化的道路。

【余东海】东海态度(四)
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儒家的,我的思想、仁本主义思想就是儒家思想。
-88.jpg!cover_160_120)
【杨朝明】今天应当怎样研究“孔子遗说”
任何学术问题的探讨都应首先解决资料问题,孔子儒学的研究也不例外,资料问题尤为重要。由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评价与态度。而从根本上说,人们对孔子褒贬不一,是源于对“孔子遗说”的不同认识与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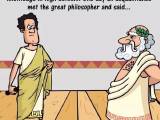
【阿格尼斯·卡拉德】哲学家还搞什么请愿签名?
哲学家的工作靠的是论证,而不是靠发挥影响力。

【余东海】东海态度(三)
思想争鸣、观点辩论是君子本分,传正理扬正义弘正道,破歪理辟邪说放淫辞,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自立立人自达达人,都离不开争鸣辩论。任凭谬论雷鸣而不辩,眼见真理毁弃而不争,或者将义理之争转换为意气之争,将同仁间正常的道理争鸣转换为恶意的道德攻击,都是有失儒家身份的。

【余东海】东海态度(二)
东海主张去马尊儒,实属救世心切。因为我深深地认识到儒家文化普适天下万世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唯有儒家才能从根本上救民救国,道援天下,最终实现太平大同理想。故知其不可而为之。这里的不可有二意:一指不利于现世之个人,二指不适宜现实之社会。救民不惜蹈危地,弘道何妨屈自身。

【田飞龙】反修例运动与两制融合难题
大游行及七一风暴标志着占中范式重新归来且有暴力升级,也标志着中美贸易战下“香港牌”再度升温,更折射出香港行政主导制的现实困境及中央在港管治能力的结构性短板。

【亨利·勋伯格】从猿到人再到超人
本文认为,我们的下一步是学会接受自我。
-128.jpg!cover_160_120)
【项阳】由钟律而雅乐,国乐之“基因”意义
中国当下所见能够相对完整演奏五声和七声音阶的乐器应从贾湖骨笛开始,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挖掘出数批、计数十支新石器时代早期6—8音孔骨笛后的认知。先民们的乐器实践,必有乐律理念生发。

【陈苏珍】自然与心性的融合
善恶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先秦以来孔子、孟子、荀子、杨雄、韩愈等均从观察、归纳和解释经验现象出发,聚焦人性善恶的讨论。及至宋儒,始从理气、阴阳等超经验范畴讨论善恶。朱熹善恶思想集理学之大成,结合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论,从自然和心性双重视角阐释善恶,突破社会伦理层面,实现了善恶本体意蕴的哲学建构。

【余东海】东海态度(一)
欲向我学儒,欲与我交往或争鸣,欲对我进行批判,欲为儒家取精去糟,都应该对儒家思想有所了解,也欢迎对我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态度有所了解。兹将有关“态度”的部分微言汇集于下,聊作自我简介,供有志之士参考。

【马特·里克】翻译的重担
书是装满了各种期待的怪异容器。书出版时会想象读者的存在,如果出版了之后,没有读者阅读,这本书就让有些人遭受金钱上的损失了。

【余东海】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
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为政,以力服人者,恶道也;以力假仁者,霸道也;以德服人者,王道也。为人,以力服人者,暴力分子也;以力假仁者,伪君子也;以德服人者,圣贤君子也。

【田飞龙】香港反对派施暴者必将付出高昂代价
连日来,香港反对派激进分子不断刷新暴力破坏行为的下限,对香港法治与民生利益造成持续性损害。8月11日,香港发生多起暴徒用汽油弹袭警事件,包括湾仔警察总署、深水埗、尖沙咀,其中尖沙咀警署袭击事件导致一名警员受伤,这不仅有着进一步暴力升级的意味,更有着将示威活动变质退化为“港式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曹海东、彭杨莉】乾嘉学人的目验之法
乾嘉时期,学术研究极重实证,讲究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学人们因而十分信重目验的治学方法。如段玉裁说:“凡物必得诸目验而折衷古籍,乃为可信。”(《说文解字注》“梬”字注)
-87.jpg!cover_160_120)
【田飞龙】止暴护法是香港解困正道
香港反修例运动已经明显偏离了“逃犯条例”的最初聚焦点,演变成一场瘫痪香港管治权并极限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政治反对运动。这场运动以“无大台”的青年学生为主,以周期性“游击”方式与不断升级的暴力冲击行为刷新了香港社运激进化的纪录。
-1.jpg!cover_160_120)
【夏国强】《论语·八佾》“文献”礼源考
“文献”一词,在传世典籍中首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127.jpg!cover_160_120)
【吴笑非】晚明實學述
道學之有明學,猶漢學之有古文也。今文專經,古文博物,道學精微,明學宏大。蓋草創多質,繼起多文,先覺多分說,後學多合參,必然之勢也。道學雖繼唐而主文,宋末集成日淺,故弟子不敢放手。

【齐义虎】法治中国化是依法治国的第一要务
按照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法律乃是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法律传统。故法律可以借鉴,但无法移植,不经过中国化的洗礼,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或者迷信西方的原教旨主义,都无助于法治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