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钩】种世衡巧施连环反间计
北宋庆历二年秋,西北沿边诸路都在传言“元昊为西蕃所败,野利族叛,黄鼠食稼,天旱,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思纳款”。知延州庞籍趁机叫人给元昊的部将野利旺荣写了一封信,招诱他投诚:“倘阴图内附,即当以西平茅土分册之”。知渭州王沿也派了僧人法淳,带着书函与金宝招降野利旺荣的兄弟野利遇乞。

【丁纪】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
诗可谓“很阳明”。两句在此诗之中也自好,良知之不假安排、浑然天成也自是,但说着便将良知与物理相对,则此对者非彼“世儒”,恰阳明先生自己也。诚不知“物理”也者,正“根本”之所在,非但“支流”而已矣;而“良知”之云倘不在乎理,则秉彝之一点惺惺,固不足以为“根本”矣。

【李强】郭齐勇先生和他的“守先待后”之作 ——简评郭齐勇著《传统文化的精华》
近代中西遭遇以来,西方挟其器物、制度乃至观念的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压倒性优势。一时间,传统中国要走向现代,突破其困境,中国文化成为众矢之的。自此以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不同于西化派全面否定、全盘打倒的“彻底重建”,郭齐勇先生强调在传统与现代双向批判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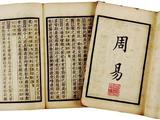
【张其成】从《周易》看君子人格两大特征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也是君子文化的早期集大成之作。《周易》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到战国。《周易》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经文部分形成于西周早期,传文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经文部分称为《易经》(狭义),是蕴含哲理的占卜书;传文部分称为《易传》,是超越占卜的哲学书。

【孙仲兹】坤道之僭越
“乾坤”与“阴阳”是人所熟知的概念,虽则如此,人却常难说清二者的区别——或者以为二者并无区别。其实凡论阴阳,都是就物与物的差别而言,论乾坤,则是就物与物的关系而言。一如孔子所谓的“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所谓乾坤关系,就是一者以身作则而全无施为,一者效法前者而不自主张,二者各致其德却又协力成功···

【陈瑞泉】发挥高校雅乐教育的时代价值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挖掘、传承和创新发展儒家音乐文化精神,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近年来,曲阜师范大学作为国内儒学研究的重镇,继往开来,不断推陈出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以下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儒家音乐文化进行了解读,深入探讨了儒···

【孙甜甜 张建平】感受儒家雅乐的“中和之美”
儒学是教化之学。为达成道德教化之目的,儒家特别推重“礼乐”,故其有“礼乐教化”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虽合用“礼乐”以行教成化,然“乐合同,礼别异”,“礼”和“乐”发挥教化作用的形式却是有区别的。大体而言,礼使人有差有别,乐使人有合有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儒家的“礼乐之道”,如果说,其“礼”论思想中蕴含着一种“···

【武宁 艾峰】关注儒学视域中钢琴艺术的中国化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心魂”。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虽然其理论形态与内涵随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演化,但儒学的精神却一脉相承,并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因而对近代以来不断发展的钢琴艺术亦有深远的影响。

【王锺陵】对立与融合:论《庄子》与儒家思想
儒道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论题。论者们发表过种种意见。魏晋玄谈中有“三语掾”的故事:“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

【陈力】学贵力行:孔子思想的可贵品质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古人尊孔子为“圣人”“至圣先师”等。孔子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还有学贵力行、躬行践履的精神,他以勤奋学习、勤勉修身、改造社会为己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知识、增长才干,创立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

孔学堂年终盘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心灵 ——贵阳孔学堂市民公益讲座走过800场
“今年是张载诞辰1000周年,张载既纠汉唐儒学之偏,又辟佛老之失,并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以及诚与明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问题,这不仅开启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新思路,而且还规定了宋明理学发展的新路径……”

【虞万里 漆永祥】《五礼通考》终于有了整理本
五礼是中国古代礼仪的总称,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清代成书的《五礼通考》对中华礼制作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总结梳理,被称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百科全书”。

【张鑫】明清时期的皇帝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不仅民间广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流传,即便是“受命于天”“富有四海”的历代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而明清时期的传统中国已经进入了帝王教育制度和文化集大成的阶段。

【田飞龙】BNO法律变质之争的源起与终局
BNO已成为历史陈迹,是大英帝国“殖民遗产”与“殖民情分”的谢幕礼。中英从1984年外交备忘录的妥协到2021年最终分道扬镳,折射出“一国两制”国际政治环境与条件的激烈变迁。国籍法与法律身份的清晰化,表面上是中英法律斗争及香港部分居民旅行权利的减损,实质上是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与基础立法者宪制角色的理性展现。

【孙仲兹】略论《太极图说》与《周易》之抵牾
本文摘自《格物学》,为物理篇之附录。

【丁纪】主一无适续
明日,慧琳之二隅、三隅至。

【方旭东】“远者来”:关于外来移民问题的儒家智慧
移民是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中国的国际移民也日益增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来移民的接受显得十分保守。无论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个局面都亟待突破,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则是对外来移民的认识问题。古典儒家处理外来移民的智慧值得借鉴···

【陈来】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主编的《陆陇其全集》。陆陇其是清初的朱子学家,号称理学名臣。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将会有重要的推动。进而言之,我觉得明清朱子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将会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

【肖群忠】中国亟需建设丧假制度
现代孝行,不仅要在道德文化上给予倡导弘扬,还要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支持,尽量不要出现这种现行规章制度甚至法律与行孝服丧送终的矛盾。解决这个冲突的现实可靠办法就是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启动丧假的立法程序,这虽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应该立即着手进行。

【肖群忠】中国亟需建设丧假制度
现代孝行,不仅要在道德文化上给予倡导弘扬,还要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支持,尽量不要出现这种现行规章制度甚至法律与行孝服丧送终的矛盾。解决这个冲突的现实可靠办法就是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启动丧假的立法程序,这虽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应该立即着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