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法生】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

【匡钊】论孔子与其后学的精神修炼
孔子对仁的追求,可由“爱人”与“自爱”的维度加以审视,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在”方式,如作为精神修炼技术的“内省”与“忠恕”。孔子后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最重要的功夫论话题,即有关于“诚”与“独”的思考。这些作为孔子后学精神修炼的关键,最终要求我们以真诚的方式保持内心的完整性,并以此作为获得德性、达成理想人格···

【陈志伟】虚灵、实理与气禀:朱子论心、性、情
朱子重新解释了心、性、情三个范畴的含义、特点和效用,认为心是虚灵明觉,具有统摄义和主宰义,性是实理,其内涵是“合当”或当然之理,即规范性和正当性的道德指向,而情则是心之已动和性体的发用,因此属于气禀的范畴,气禀精粗和正偏导致情有善恶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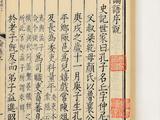
【刘军】朱子注解“新民”的理论逻辑与历史意义
朱子注解“新民”遵循了“以文义推之”与“以传文考之”相结合的原则,其逻辑思路为:人人皆有明德处且需要自明其德,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民的可能性;新民的重要性和“民”自身难以完成自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从总体上决定了新民的必要性;新民的实现需要“上之人”与“下之人”共同努力,综合运用“絜矩之道”“齐之以礼”“齐之以刑”,始终坚持“苟日新、···

【尚文华】利玛窦理性观和儒家天命观在善问题上的差异与互动
在终极性意义上,为善无意为为善有意提供了存在意义上的终极根据;并且前者也时刻以“不”的方式参与进后者的“是”之中;它们一起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生存本身。生存本身照见了利玛窦式理性论证和儒家天命意识之间的差异和相互补足,这是实现中西之间深度思想交融的关键所在。

【苏晓冰】王阳明与理学中的道统问题
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将“十六字心传”看作是“尧、舜、禹所传心法”,标志着理学在实质层面上开启了“心学”这一儒学新路向。阳明的道统论与其心学构建则是接续理学的道统论及其所蕴含的心学路向展开的。在阳明那里,道统是在历时性的时间脉络中确立儒家学术的精神命脉,而正统则是在共时性的多元学术形态中贞定儒家学术的发展方向。

【秦际明】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

【王化平】民本与人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

【傅锡洪】“形”的哲学:张载思想的一个侧面
古代东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不乏对人的身体和知觉予以负面评价的。在宋儒张载那里,形(质、形质)和知觉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有关形的论述构成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宇宙原始的混沌之气必然发生聚散的分化和对立,这就使形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这是对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幻妄之观点的直接回应。

【陆畅】记忆与遗忘: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的内在张力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

【杨儒宾】体用相待的本体论——道体论儒者的选择
道体论者的体用论却非如此,他们的形上—形下的结构不是套套逻辑的恒真式构造,而是形上—形下互涵,形上既是完美自足的,但同时也要自行创化的。落在道器论上讲,即是道器相涵的形上学,道的内涵有待器来补足;器的内涵,其本质也是流动的,它是“流形”,它需要作为本体的道的支撑。

【姚海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思之有得——郭沫若的荀子研究平议
郭沫若荀子研究散落于其20世纪30、40年代的多篇作品之中,涉荀研究持续时间长,对荀子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较高关注度,产出成果丰硕,属民国荀子研究的精湛之作,极富思想史研究特色。

【姚海涛】逻辑曲解与思想误读:叶适对荀子批判之平议
叶适的批判具有逻辑曲解与思想误读的鲜明特点,在当时及后世,非但对于阐扬荀学无功,反而融入了贬抑、解构荀子的“反荀”思潮,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流弊。

【王钧林 王法强】成人、齐家与化俗:家礼教化功能探析
家是儒家开展人伦教化的核心场域,家礼则是维系家庭或家族和谐稳定的伦理观念与仪礼规范的综合体。伴随着家形态的发展演变,家礼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完备,并由贵族而普及平民百姓,成为指导人们日常居家生活的各种礼仪规范以及冠、婚、丧、祭四大人生礼仪。

【林桂榛 王雨】汉字“美”源流综考与中国美学基本体系辨略
“美”字的源起表明古人的美观念起源于视觉形象及视觉心情,并非是起源从“大羊”或“羊大”的味觉义。“美”字初指人形象好而令感官喜悦,但今作价值概念早已超越对视听价值的指称,佳好者尤感官感觉好者皆可语称为“美”。美学的基本内容或基本体系主要在美的概念(语文)、美感机制(心理)、美治机制(工艺)、美的学说(史论)四方面,一切···

【丁鼎】“《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

【张士杰】儒学日本化的政治伦理向度探微——以荻生徂徕之论“学”为例
荻生徂徕《论语》诠释具有显明的政治伦理向度与本土契合性逻辑,是近世日本儒典在地化阐释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亦可视为儒学日本化进程之重要一环。其内在逻辑及本质意义,是在学、德、政之意义逻辑上,展开选择性接受和变异性阐释,从而将儒学内在化于本土学术文化范畴,建构具有本土契合性和当下关切的政治儒学。

【邱振华】默识与体认:薛瑄的穷理工夫论
薛瑄重视默识的概念,是因为贯通性与天道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薛瑄对默识工夫的重视,可以看出他在工夫论上明显有注重内向体验的倾向。薛瑄对默识概念的使用仍然是继承程朱,他所说的默识并不单纯指默坐澄心、体验未发的工夫,而是兼具内外的默识心通。在薛瑄的工夫论中,默识与体认又是相通的概念,默识主要是心地工夫,体认则···

【胡游杭】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

【陈赟】“道事合一”: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实践性和开放性
“见之于行事”作为中国历史意识的原则,内嵌到中国的经史传统之中,形成了不是以空言(概念、理论、学说等)显明道义,而是即事明理、寓道于事的“道事合一”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意味着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在道与事之间建构的原初关联,道的显现不能脱离人所行之事,道之显现优先于道之存在,以事显道凸显了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实践品格。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