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利安·克罗克特】《失败颂》与讲故事: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访谈录
本文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则”系列访谈的第一篇,该系列访谈专门探讨人类依据一整套不断变化的法则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访谈的对象是那些提出生存法则的人或者深入思考生存法则并寻求扭曲或破坏它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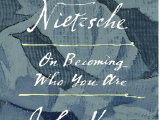
【克里斯平·萨特维尔】新希腊主义
卡格又出版了一本书《尼采一起搭车旅行》,这是一本集游记、回忆录、通俗哲学于一身的作品,永恒轮回主题被纳入其中。他将理解尼采哲学的工程变成了令人愉悦的快乐享受,虽然书中也谈了卡格面对自己的黑暗时刻的很多痛苦。

【戈登·马里诺】探索死亡的诱惑力:克兰西·马丁著《如何不自杀》简评
对于那些有着神秘恼人的感受,认定人生就是一场诅咒的人来说,《如何不自杀》是激动人心的、引人入胜的读物。马丁是苏格拉底协会的少数成员之一,也是技术高超的小说大师。

【文森特·劳埃德】斗争哲学
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并非所有灾害都是可以修补的,无论这灾害是发生在动物身上还是土地上,或者是曾经被殖民或者被奴役的人身上。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未来一些年将认识到是我们造成了灾难,而且还在制造新的灾难,但我们尚未意识到其严重的破坏性。

【乔治·斯夏拉巴】自由主义的两面
过去40多年,情况发生了改变:如今随便走过一个街区你很难不会遭遇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批评家们有怒目圆睁的自由女神支持者,推崇自由市场的自由意志论者,新古典经济学家,新伯克派保守主义者、天主教融合论者、批判性种族理论家、后现代主义者,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者。

【基兰·塞蒂亚】哲学家的气质
梦想是阅读这样的哲学家的作品或者成为这样的哲学家,其观点既是成功的自我表达又能描述事物的真理。他们的著作探索了气质同时揭示了真理。只要它符合情感习性---郁郁寡欢的、冷静不冲动的、暴躁易怒的、乐观主义的---这种气质与现实吻合的事实意味着某些对待世界的情感特征是客观存在。

【克里斯潘·萨特维尔】后语言学转向
我们不再是新闻报纸泛滥的星球,而是一个想象和视频图像文本杂合体的世界,这是《逻辑哲学论》没有涵盖的东西。我们现在似乎更关心我们是否生活在虚拟现实中而不是生活在文本中。但是,产生的各种新问题都在要求我们新思考,而且也在创造新历史。

【亨利·吉鲁】黑帮资本主义与法西斯教育的政治
黑帮资本主义之所以横行霸道就是因为受压迫者的沉默以及它与被权力诱惑者的勾结共谋。

【西奥多·达林普尔】公爵与肉贩
在我的体验中,冷漠和蔑视对他人的伤害和制造的痛苦比不公不义更大,更严重。毕竟,不公不义是能够纠正的,而冷漠和蔑视造成的伤害更深。它们意味着,你根本就不配得到考虑,不配被当成人,而不公正对待的人至少承认你的存在让他感到不满所以让你受了委屈。

【阿格尼斯·卡拉德】爱欲魔鬼
在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浪漫爱情期间,我常常幻想为这种关系举办一次葬礼。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给出了这个幻想涉及到的各个细节:我选择了一个场所,想象和亲密恋人的结合,挖一个坑把他送给我的所有东西——大部分是书和信——埋起来,留下一卷还没有读的书权当墓碑。

【詹妮弗·拉特纳·罗森哈根】失败的慰藉
对于讨厌将世俗成功作为道德优越感标志的文化的那些人来说,布拉达坦的书是一种滋补品。常见的口号“赢得胜利不是一切,是唯一之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证明这个社会贫瘠平庸的证据。

【贾斯汀·伽尔森】疯狂哲学是什么?
笛卡尔既然愿意承认所有怪异的可能性的存在,他本人陷入疯狂的可能性为什么就是不可思议的呢?福柯给出的著名论证是说,笛卡尔给出了哲学和疯狂根本上分隔开来的声音---哲学,至少是西方哲学一直遵循这种传统。

【帕特里克·韦斯特】为后现代主义辩护
福柯拒绝身份认同政治并不令人吃惊。毕竟,他拒绝固定不变的、稳定的范畴观念。这和其他后现代思想家们一样。就像福柯本人一样,将他们描述为“自由意志论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浪荡公子”可能更好些。毕竟,无论你认为福柯和德里达是什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家。

【艾伦·莱维诺维茨】使用智能手机之道
我们从来不缺乏创造性的窍门来修复人与智能手机破裂的关系。消费是敌人,限制是解决办法,新习惯是人家承诺的结果。目标呢?更具生产性的生活,让人摆脱无用的浏览和空洞无物的社交媒体光顾之苦。

【伊丽莎白·拉什·奎因】什么也不能像失败那样成功
想到死亡令人如此痛苦的理由是,无论是自己的死亡还是他人的死亡,每个生命之前和之后不是那没有终结的虚无,相反,是它那简单的庞大无垠,虽然有人可能说因为我们不可避免要遭遇的痛苦:导致个体存在的种种特殊性的众多时刻,填补我们生存时刻甚至多得溢出来的种种错综复杂之事。

【里弗卡•温伯格】死亡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各位读者朋友,时间就是个杂种:与她交往没有意义,不与她交往同样没有意义。认识到时间是让人生变得有意义或无意义之物能够让我们减少一些对死亡的痴迷,更容易与人生中的大事达成和解:需要活着的那段时间。

【斯蒂芬·安德森】偶然与幸福
毫无疑问,我们在物质上更富有了,在周围环境上我们也得到更多的庇佑,但是,如果有什么的话,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加焦虑,更加不满意,在情感上更加迷茫无助不知所措,难道不是吗?

【格温德·林·格雷瓦尔】死亡时尚
“时尚”这个词往往让人毛骨悚然,背脊发冷。我的意思不仅仅指知识分子而且指普通大众。时尚为虚荣心、消费主义、肤浅薄情、女性化、诡辩术、江湖骗子擂鼓助威,使其大行其道。当然,听到“时尚”这个词时,你大概不会想到哲学。

【罗布·博迪斯】痛苦政治学
疼痛经验并非人类独有的东西。疼痛有悠久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动而有所变化。详细阐述这个历史能揭露人类痛苦的政治学,它位于人类衡量、确认和抛弃痛苦体验的各种尝试的核心。

【德安博】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著《失败颂》简评
《失败颂》将在每个读者身上激发批评性反思,为其提供一点儿都不狭隘的教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它不是对自我以及现有观念和感受的称赞和恭维,相反,它以愤世嫉俗的、令人担忧的、可能带有救赎色彩的方式挑战我们的成功假设:你可能失败,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