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点我丝毫不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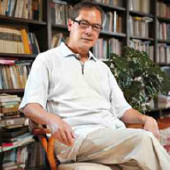 |
何怀宏作者简介:何怀宏,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江西樟树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道德·上帝与人》,《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等。 |
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点我丝毫不怀疑
原标题:当代中国的道德重建,路在何方?
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采访:王淇(共识网编辑)
来源:共识网,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二日甲辰
耶稣2015年7月27日

嘉宾简介:何怀宏,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翻译多部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译文信实流畅,对国内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代表作《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道德、上帝与人》《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普遍共识
王淇:从良知论到底线伦理、新纲常,您一直致力于提出现代意义的道德规范。学者提出的规范如何才能成为社会共识,并落实到实践中?
何怀宏: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学者做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尝试提出一些他觉得可以成为共识的观点。这个过程可能是不断的,要依赖知识的训练,也要依赖直觉。他首先要考虑和论证有没有某种具备普遍性的共识,有没有我们生活中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的学者,他觉得世界上不会有什么普遍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的,哪怕是想要否定这种普遍共识的人,他们也认可要讲道理。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说理来解决问题或影响人呢——至少希望如此?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有一些东西能够得到大部分人赞同的。要通过说理而不是暴力和欺诈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共识性的前提。为什么要靠讲道理而不是靠拳头、靠谎言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尽量互相说服?那怕惩罚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惩罚?学者说出理由来——我们都是比较平等的存在,你不能去压服别人。这其实已经隐含着一种道德含义了,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立法”,你要想一想它能不能成为所有人都这样做的行为准则,它能不能成为普遍的法则?我不希望别人伤害我、杀戮我、欺骗我、凌辱我,那么我也不应该这样对别人。这就包含了一种基于平等的普遍性。
另外,不要说规范,即便是事实也是会有例外的,你试试给人下一个一个有关人的事实的定义:两足无毛?有意识?有理性?人是能够使用工具的动物?任何一个概括都会是有例外的,但难道我们就不能尝试对人做某种概括以将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个别例外推翻不了这些基本事实。规范也是如此。人要合群生活,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某些做人的基本规矩的。
平等不是家庭伦理的最高价值
王淇:家庭教育在伦理重建方面起很大作用。现代家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生存常常亲子相离,这种情况下和谐的亲子关系何以保证?又如何处理平等与孝顺的矛盾?
何怀宏:我们在公共领域(尤其政治领域)讲究权利平等,在家庭领域也讲人格平等。父母对孩子要尊重,哪怕是他们养活他,但在人格上也应该尊重孩子。
但是平等的原则,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贯彻程度不太一样。在家庭里,我觉得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权利平等或者关爱平等。通过血缘和婚姻结合起来的家庭,有一种本于自然的不平等。孩子幼小时经济和教育都依赖父母,父母衰老了生活上也依赖子女,所以家庭中的话语权是会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甚至不平等,一般情况下会通过感情来弥补。比如在家里会对最弱的那个成员有更多的关爱,这是很自然的;再比如孩子的心智成熟有一个过程,父母还是要有一定的权威,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商量;还有老年人会变得跟孩子一样,所以儿女要学会去理解。
其实到了21世纪,父母对子女的压迫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子女的工作、婚姻,他们也会想提意见,但是包办不了。越独立越有出息的儿女,越是觉得父母对他构不成权威。相反,倒是现在都是儿女本位,父母没有多少话语权。所以儿女要更多地关心父母。
另外,恋爱、婚姻乃至家庭的确不是现代社会伦理调节的主要范围,甚至有许多不在这个范围。所以,在这些私人生活领域会有广泛的多样性。只要当事方都觉得舒服,也不伤害其他人或妨碍社会就可以了。
王淇:五伦里面有一伦是兄弟姊妹关系。这在原来独生子女政策下一直欠缺。现在政策放开了,前一阵有新闻说头胎反二胎,家里多了弟妹似乎就分了父母的宠爱。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悌道?
何怀宏:有一个兄弟姐妹,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父母要引导小朋友这样想,不是说分爱,而是有了陪伴。就像歌德所说的,人到这个世界上,一生能够接触到的人并不多,其中能成为朋友的也不多,变成亲情关系的更少了,所以你要特别珍惜。
独生子女长大成家,工作、父母、儿女,几方都在牵扯你的精力。其实很不容易。如果有兄弟姊妹,至少不会如此焦头烂额。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有相当的距离,过去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现在可能亲人之间也淡如水。那么调整的方式就是,父母要尽量开明,鼓励儿女自理生活和感情;儿女要尽可能兼顾事业和家人。
语文课和作文题有道德养成的意义,要慎之又慎
王淇:学校教育方面,您好像比较关注语文课。语文教育如何在伦理重建中发挥作用?
何怀宏:对,我现在对学校教育有几点感触。一是德智体不平衡,中国的教育始终太强调智力,德育往往政治化而不是真正的品德教育,体育好像变成附属科目,更不受重视。
体育在国外许多国家是放在第一位的,尤其男孩子身体要健壮。智育也不如民国时。那时候很多大学者教师范、教小学,现在小学老师能是大学者么?可能的确有少数的很好,但再也不会像晚清乃至民初那样重心在下,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在乡土了。
城市里是这样,农村就更糟。我一方面很同情乡村教师,待遇不好,就像有人说的:可能就比乞丐高一点;但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也远远不如以前。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城乡择校都那么厉害。
语文课是可以让孩子在学习文字的过程中养成道德意识的。不过现在的语文教育真是有问题。你看高考这个指挥棒,作文题水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拔高,道德上拔高,政治上拔高,精神上拔高。
比如说那个作文题,父亲违反交规子女该不该电话报警。首先,这个题目对农村孩子不公平,他都没有这样的体验;其次,报警还是不报警,你让孩子怎么回答?高考那么重要的事情,孩子就要想出题人希望什么答案。似乎报警才是政治正确,说心里话就得不到好成绩,这不是让孩子为难吗?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标准答案,最好没有。
高考题作文题反映中等教育总体的水平,出题人怎么想会构成某种引导。所以要慎之又慎,尽量平实。
品德课上的榜样,最好不要是政治领袖
王淇:您刚才也提到学校德育课程是政治化的。那么能够引导孩子们真正确立起道德信念的德育课是怎么样的?
何怀宏:小学德育的内容就是很基本的东西,比如说诚实、有同情心。最重要的一点,品德课教材的例证、故事最好不要和政治人物发生关系。普通人的例子就很好,不要动不动就和某个革命领袖、英雄人物联系起来,也不要那么壮烈的事迹。
一个普通人做到了本应该做、但对他来说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就很了不起了。比如说借了人家钱应该还,但确实有困难,最后想方设法还清债务类似这样的小事情。
另外品德教育的方式不一定是上课,也可以通过一些活动。
到了中学,应该有公民教育。孩子长大,进入公共领域,要成为一个公民,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等等。你希望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所以你要承担起责任。现在一提公民社会就紧张,我很奇怪。共和国最需要公民的道德,最需要好公民。
王淇:大学的德育课程呢?桑德尔讲公正的公开课很火,跟大家一起讨论道德困境,您觉得这种方式会是好的品德教育吗?
何怀宏:我觉得至少是一种很不错的方式。但它不是唯一的,也不能取代其他方式。老师在教学中注意倾听学生的想法,这很重要。老师得让各种观点都有展露的机会,让各种道德选择得以呈现。不要轻易评价对错,而是慢慢引导大家思考什么选择才是比较恰当的。
对师德医德可以有高要求,但不能太不近人情
王淇:近些年媒体曝出很多师德问题,社会上对老师这个群体也有特别失望的感觉。师德怎样提升?
何怀宏:一方面因为面对孩子,可能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有特殊的伦理要求,得比其他职业高一些。老师掌握着话语权,行为出了问题会影响很多人,而且孩子有时候没办法反抗。所以对师德有特殊要求甚至更高要求都是对的。
另一方面,社会上普遍都对老师、医生这些职业,有很高的道德期望高。但这个高期望也要恰如其分。老师也是人,所有行业都平等,不能一说起老师就是灵魂的工程师,指望他们像蜡烛一样烧尽自己照亮别人;一说起护士就是白衣天使,舍己为人。不能把这些职业太神圣化。
因为专业知识的权威,老师、医生、护士面对的人群都比较弱势。所以可以对他们提出特殊的道德要求,但是不能把这个要求拔得过高。
现在老师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很低,民国时期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比县长还高,现在可能吗?那么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老师也能过一种像样的生活?提升收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老师也要进行业务培训,包括道德方面的要求。师德不好的人,可以干别的,不要做老师。
包括医生收红包的问题。现在红包都成一个潜规则了。医生拒收,病人还不放心。别人都送了我是不是也得送?当然也有病人以红包的形式表达谢意和对医生手艺的尊重。已经形成风气了就不太容易变。以后得慢慢改。
行业伦理最好是自觉充分地讨论才能形成
王淇:南都记者卧底高考枪手集团这个事出来后,争议集中在记者有没有违反伦理。行业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应如何形成?
何怀宏:高考是决定很多孩子命运的时候,枪手代考对那些诚实考试的孩子,是非常大的不公平。相对这样大的危害,卧底的记者哪怕有不妥的地方也次要得多。因为他可能没有其他的发现手段。高考影响成千上百万的考生和家长,需要采取特殊手段来遏制枪手替考这种现象。记者伦理里应该对这种情况预留出空间。
行业共同体的伦理规范,不一定是国家自上而下制定,可以通过行业自觉讨论形成。
道德是靠实际践行磨练出来的
王淇:前面讨论了那么多具体问题,现在来聊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阳明的弟子问阳明,为什么一个人知善恶但就是不能行?阳明回答说因为不是真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何怀宏:我觉得阳明说的还是很有道理。你如果真的知道了善恶,就会产生一种信念,觉得这是天经地义。像康德所说的,“义务是压倒性的”,之所以叫义务就是你必须如此做。这样你一定能够克服障碍,克服利益的诱惑。
如果你仅仅觉得好像道理是这样,却没有真正地从内心里把它看成天经地义的东西,毁犯了就不安后悔。那你确实还不是真知。真知是把意志、感情、理性结合为一体。古希腊哲学家说,人除了理性,还有情感和意志。当你理性上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但你从情感上、意志上接受不了,这就不是真知。加入了情感和意志的理性,才是知行合一的真知。
这个知,不是说我在这里冥想,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相反,你要靠意志靠行动培养你的道德信念。行要靠真知,知又要靠行动笃定信念。有时候你可以试着做一件不太情愿的事情,一旦做到了,你就发现上了一个台阶。本不情愿,但就因为它对,所以我去做。那么我就不是一个意志软弱的人。坚定的道德意志,需要行动的力量去培养。有这么一次经历,你就会发现后面碰到类似的事情就容易多了。所以道德是要靠磨炼的。知行合一就是要把知和行结合起来,在事上磨炼,不仅是在心念上,在思想上。
道德需要制度保护,法律尤其不要伤害好人
王淇:除了内在信念之外,道德是否需要制度支持或者是物质激励?
何怀宏:肯定需要。我还不说物质激励,先说基本的物质保障。有的人见义勇为受伤了、残废了,甚至死了,他的家人怎么办?应该有一些制度,能够让他的身体、他的孩子有一个基本保障。
但道德一定不是靠物质去引诱和激励出来的,因为真正的道德发自内心。道德的下手处是做到绝不干那些不该做的小事情,而不是说一上来先去做那些特别难、特别高尚的事。但有人做到了高尚,就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这个更多的是事后奖励还有事后弥补,形成制度,使见义勇为者不至于过分担心。
所以道德需要制度的保护(包括法律、经济、保险等等)。制度不要损害道德,法律尤其不要伤害好人。这个“不做什么”很重要,而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使人们不去做某些事情,不是无所不为,无法无天,这个可能更重要。
公德禁令要考虑人们的实际需求
王淇:北京出台了最严禁烟令,有观点认为这侵犯到私领域的自由,您怎么看?
何怀宏:禁烟也要考虑到一些需要,不能完全一刀切说凡是有屋顶的地方一律不能抽烟。比如在机场,有时候飞机晚点几个小时,外面又下着雨,一些烟民又不能出去抽烟,就可能受不了,就可能闹了。是不是可以专门辟出来一个抽烟室?既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又不会打扰别人。
再严的禁令,如果不能真正贯彻执行,就得考虑会不会造成新的问题。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湖边看到“严禁游泳”的标语,结果也没人管理。很多人下水游泳,这样就很反讽。久而久之,大家就对法律规定失去了尊重。如果做不到监管,索性就不要这块牌子了,不然变成对法律的嘲弄。另外有些河确实需要禁止,但是有些河是不是也可以开放?
法合乎道德,守法才变得容易
王淇:您曾在《底线伦理》中谈到:“现代法律只有从根本上被视为是正义的、符合道德的,才能得到人们衷心的尊重,才能被普遍有效地履行。”法律能不能贯彻执行取决于其道德基础是否坚实?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怎样?
何怀宏:法治国家一方面要靠法律本身,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而且量法适度。违反法律的行为肯定要受到相称的惩罚,这是一个推动法治的措施。如果有法不依,违法也受不到惩罚还得到好处,我干吗尊重这个法律?
另一方面法治要靠道德,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到的地方,我还要不要守法?整个法律体系要使人觉得基本上是正义的,也是保护所有人的,而不是保护某些统治者或者少数人的。那这样人们守法才会有信心。因为今天虽然法律让我感到不便,但是以后在类似情况下它使别人不至于伤害到我。只有这样,即使今天我感到不便,我也遵守法律。这是一个道德的支持,甚至有时候还有宗教的支持,精神的支持。
为什么苏格拉底即使觉得被判处死刑很不公正,仍然遵守判决上刑场?就是因为他认为雅典的法律体系基本合乎正义。市场是个信用系统,法律也是个信用系统,它只有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运作。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守法的人好像有点傻,如果大家都这样想,这个法律体系肯定是贯彻不下去的。
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点我丝毫不怀疑
王淇:现在国学很热,有学者提出了儒学应在政治建构上有所作为,您怎样看?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之争,您又怎么看?
何怀宏:港台儒家和大陆儒家确实侧重点不一样。港台儒家在心性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政治的需求不迫切。这也跟香港法治或者台湾民主状况比较好有关。很多东西都实现了。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从革命的年代过来,“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否定我们的传统。所以大陆儒家对于儒学更看重政治建构的部分。这是两岸的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他们问题意识不太一样。
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点我丝毫不怀疑。为什么?不光是儒家在历史上确实有作为,它给政治提供了一种人道价值,政治不仅仅为了君主。我不认为儒家思想自己能开出民主,但是它肯定能够缓解残忍和专制的东西。王道、仁政,这是它一直强调的。
儒家一直试图限制君主权力,至于手段是不是有效,这是另一个问题。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制度,比如法治、民主、舆论监督等等。但儒学的核心价值仍然能在政治领域里面发挥作用,它对生命的尊重、对暴君的谴责都非常有意义。只是我们也不用夸大这种作用。儒家还是可以提供很多资源的,尤其在社会建设、道德建设方面,自我修身方面更是如此。
儒家不一定对抗权势,但应该保持警惕
王淇:儒家传统怎样解释自己和革命新传统的关系,这是当代儒家需要面对的问题。您会怎么描述二者关系?
何怀宏: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反传统的新传统,当然二者之间存在对立,不可能一下就调和起来。我觉得这需要思想史的梳理。比如说儒家主张“仇必和而解”,而革命理论强调阶级斗争斗到底,这两个就完全不可能结合起来。所以要看到这两种传统的紧张、矛盾和冲突。
现在执政党其实也已反省乃至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们可以赞许这样一种否定,不管它来自哪里。不要说凡是来自政治权力的举动都是不好的,它有这样一种态度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儒家要警惕,不能像过去那样过于相信君主的个人道德,把希望建立在圣王明君上。其实还是要保持某种独立性,永远对政权保持某种距离。不一定对抗,但是要保持距离。
罗尔斯为道德共识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源
王淇:您还有一块研究是关于罗尔斯的。除政治哲学外,罗尔斯为现代社会道德重建提供了什么可借鉴的资源吗?
何怀宏:罗尔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如何去寻求道德共识,如何把共识和信仰区分开来。
共识不可能是一个全面的、无所不包的理论,我们没办法在人生价值、终极关切、社会行为规范这些东西上达成共识。因为正当性在道德上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道德主体性,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的权利,只要这个追求不影响到其他人。
罗尔斯区分规范与价值、个人信仰和社会伦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社会道德的重建,底线伦理不能在一个很高、很大的范围内寻求,必须在一个基本、核心、底线的领域里去寻求。而且道德共识在罗尔斯看来一定是存在的,即便是道德相对主义,也认可生比死好、说理比打架好,要不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正常的秩序。所以有些东西是有普遍性的,不能说无可无不可,对我有利的时候我就遵守,对我不利的时候我就不遵守,而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遵守,这就是道德共识。
我觉得罗尔斯的贡献更多地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样的正义原则,而在于他是为我们怎么样去达到一种道德共识提供了比较现实可行的途径。
责任编辑:葛灿
【上一篇】【贝淡宁】北京:政治之城
作者文集更多
- 【何怀宏】君子的人格 12-29
- 【何怀宏 赵占居】将无同?岂无异?——··· 06-07
- 【何怀宏】我们想要怎样的人类文明? 08-11
- 【何怀宏】政治、人文与乡土 ——当代儒··· 07-06
- 【何怀宏】人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伦理道德··· 08-08
- 【何怀宏】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 10-28
- 【何怀宏】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 07-27
- 【何怀宏】抗议性政治不应成为主流 07-13
- 【新书】何怀宏:谈成功的书多,谈生··· 03-30
- 何怀宏著《新纲常》出版 11-19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