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政治、人文与乡土 ——当代儒学前景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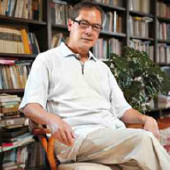 |
何怀宏作者简介:何怀宏,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江西樟树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道德·上帝与人》,《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等。 |
政治、人文与乡土
——当代儒学前景的思考
作者:何怀宏
来源:《国际儒学》2021年第1期
摘要
从历史看儒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儒学首先在春秋战国之际奠定了“学”的深厚根基,自西汉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之后,又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人文与乡土三位一体,官员一身而兼三任的社会格局。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很特别的,它保证了统治阶层的不断的和平再生产;在社会内部实现了政治的机会平等,也在政治、人文与道德风俗及社会治理方面建立了有序的联系。但是,儒家学人和思想在经过百年激荡之后,基本的客观处境是“上失其途”“下失其土”。在最近四十多年,儒学又有了一个复兴,但它也依然需要面临许多当代问题的挑战。
关键词
当代儒学;政治;人文;乡土
当代儒学的前景如何?我这里想从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做一点观察和思考,尝试从历史去看儒学的未来。这种考察不限于思想,也不限于制度,而是注意儒家学者与社会政治的长期互动关系。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能够超越他们的社会处境,甚至造成新的时势。而一般情况下的前景和趋势却常常还是会由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决定。从这方面看,尤其是又面对今天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挑战,儒学的前景并不很乐观——不太可能重新获得它的历史地位。但儒学本身也有其独立的性质、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悠久的传承,在未来还是可以大有作为。
一
我想先描述一下儒学及儒家士人在传统社会所达到的地位。
自西汉“独尊儒术”以降两千余年,儒学居于社会政治的一个主导地位。社会的上层,尤其政治的统治阶层基本都是服膺儒家的士人。他们往往一身而兼三任,首先是作为学子,通过察举和科举进入政界,成为官员或候补官员,退休以后多回到乡间,作为乡绅,依然是享有名声和威望,常常要担负解决民间纠纷的责任,以及主导建桥修路、赈灾救济等公益事业。当然,这种一身而兼三任在时间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终身也还是一个人文学者,也很可能在候补和丁忧的时候就住在乡下。
一般说来,学者是基本的资格,只有立志向学且学习优秀才有望进入官场,也只有富有学识,才能在官场享有清誉,得到衷心的尊重。即便不准备或没有机会做官,哪怕只是考中秀才,也能获得一种身份和名分,乃至享有某种法律上的优待。他们由此也进入了一个“士人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间公认和尊重的“读书人”,同时也能自然而然地在经济上获得一些利益,例如有资格在私塾任教。而如果是一旦中举,成为举人,就会进入一个更高身份的群体,直接进入政界,即便不愿从政,也可以被邀请执掌书院,或者更接近政治的职位——如参加官家修书编书,或进入某位大员的幕府等等。如果成为进士,则自然是进入了一个权钱名等资源更加优厚的群体。
在学者、官员和乡绅这三者中,成为官员或掌握权力则是关键,只有获得权力才有可能实现其政治理念,参与制定影响千百万人的政策和有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的决策。也只有获得权力,才能给士人带来财富、地位和名望,不仅成为“士君子”,而且成为“士大夫”。但要获得官职的正途和主流,还是要通过检验其学识的考试。
作为乡绅,儒家官员们则成为稳定和引导民间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作为这个社会的权威,不仅可能调解一些纠纷,解决一些民间疾苦,还常常能为乡间的文教事业作出贡献,甚至有可能在敦风化俗方面有开创之功。当年一些被贬职的官员外放到偏僻和蔽塞之地,让当地的文风开始兴起。他们也常常能够联络民间和官府,而官员对这些退休官员的乡绅也有相当的敬重,更不要说互相的雅集唱和了。他们也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多有田地和高深府宅,乡民对他们本身就有敬畏。他们本就自乡土走出,现在又回到乡土,熟悉故乡的风土人情,也不难有一种热爱或眷恋。他们过去多是农家子弟,甚至不少来自贫困家庭,比较知道人间的疾苦、奋斗的艰辛,现在他们有了一些资财、余裕和影响力,当然也愿意为改变故乡的面貌出一点力。因为有了这些乡绅,也就不怎么需要直接的政府机构,许多基层的政治职能就由他们代劳。他们根于土地,却又不是完全的“土豪”,而是曾经到外面见过大世面,更有儒学这样一种道德学问的长期濡染,也包括各种文学艺术的训练和创作,这些也相对会淡化仅仅对物质财富的追求。
二
这种政治、人文与乡土三位一体、官员一身而兼三任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很特别的,尤其是在以人文学术为进路而建功立业方面。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废除了官员的世袭制,保证了统治阶层不断的和平再生产;同时又在社会内部实现了政治的机会平等,保障了社会的垂直流动,既稳定了社会,也提拔了人才,这些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社会的治理。
西方古希腊的政治社会是小的城邦。像雅典这样的城邦,公民政治权利平等,抽签轮番为治,实行了彻底的民主,有过灿烂的文化,但是难以持久。哲学家和诗人(剧作家)在城邦内都是普通的公民,不享有特殊的地位。斯巴达享有特殊地位的则是一个武士阶层,文人学识不受待见。
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也是重武轻文。到中世纪的王国,也主要是世袭君主和武化贵族在政治上领导。但是,兴起的天主教会作为一种几乎可以与王权抗衡的力量,还是能够吸纳一些下层的文化种子。穷苦人家的有才华的信仰者,也有机会上升到高层。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为了遏制世袭官僚的弊害,直接通过强行征贡乃至掳掠一些欧洲地区的孩子,带到中心地带进行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使其成为“奴隶将军”“奴隶宰相”,执掌政治和军事治理的权力,但是也不能传后。这种制度的确不无效果,但和中国的科举相比,也就未免简单粗暴。它虽然有效地遏制了官员权力世袭制度的弊害,但还谈不上在社会内部实现了政治的机会平等,以及政治与文化的联姻。
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士人,还有一种可能的比较是近代西方,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文人学士。比如18世纪的法国,那些多为启蒙哲人的文人学士也是处在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之下的一个相对优越的地位。以其间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两位——伏尔泰与卢梭——为例,伏尔泰年轻的时候进过两次巴士底狱(当然在那里面也还是可以读书研究),后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到瑞士边境购置了几套房产和别墅,而其著述则源源不断地从那里流向全欧,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社会舆论。法王路易十五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据傅雷翻译的《服尔德传》,伏尔泰曾说:“我手上有一把王。”意指普鲁士王、丹麦王、波兰王、俄罗斯女王等都支持他。庇护他的还有更大一把欣赏乃至仰慕文化的封建贵族,另外,也因为他为卡拉等人伸冤而得到了民众的广泛了解和支持。而即便落魄如卢梭,他没有什么家产,也交恶了不少朋友,但也总是还有喜欢他的思想和才华的贵族或国王庇护者,他也时有边境的一席栖身之地、晚年回到巴黎也还能够生存。这些文人学士倒不想进入政界,但仅仅通过他们的文字,就已经可以对社会发生巨大的影响了。当然,这种影响会有其政治后果。全面地评判启蒙的社会政治后果还是一件需要仔细分析的工作。
而中国的政治、人文和乡土这三者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已经磨合出了一种相当韧性的格局乃至一种“选举社会”的社会形态。其中乡土是基础,被察举和科举选拔的人才大都是来自乡野田间,退休的官员也大多是回到家乡。乡土是来源也是归宿;是起点也是终点。就像一个循环,但却是一个上升的、光宗耀祖的循环。退休回来的官员也会关注和扶植本乡本土的读书种子,尤其是本族本家的读书后代,或又开始又一轮循环。古代社会也基本是处在一种农业文明之中,社会的重心在下,在乡村。
政治则是关键,是保障。有了权力的支持,制度的保障,才有各种资源的稳定供应。权力也是实现政治理念最有力的杠杆。尤其是中国还有跨越数千年的官本位的传统,百姓也比较习惯于服从和畏惧官员。
但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学术也是首要的,它是入口,是门槛,是必具的资格。士人最基本和原始的身份还是学者。如果不知诗书,其他一切免谈。而儒学也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学问。自从西汉采取了董仲舒的对策,在政治入仕的路径上独尊儒术,儒学就成为统治阶层的指导思想,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这种对人文的重视,也创造出璀璨的中华艺术和文化,推动着一个独具特色的“书香社会”。这样的一种一身而兼三任,反映了传统士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和关系,也表征出中国社会政治乃至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
儒家学者一般要处理三种关系:一是与自己及其群体的关系;二是与政治和君主的关系;三是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家学者在处理这三方面关系中,哪方面做得最为成功呢?
儒家的“自化”或可说最为成功。儒学首先还是一种“为己之学”,是一种希圣希贤、激励和约束自我的学问。它又不仅是自我反省和学习,同时也形成一个团体,一种制度、一种气氛。士人们在其中切磋道德学问和修身,同时也有文学艺术的润泽。士人的儒家风范到民国时期犹存,所谓“民国范”,实为“儒家范”也。
其次是对民众的教化。应该说察举和科举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发展,民间读书的风气相当高涨,在一些王朝的盛期和地区说有一种“书香社会”的气象也不为过。这在一些过去比较蒙昧的边疆地区的人文开化方面的成绩比较明显,但在如何普遍地提升人们的文化水准方面相对乏力。在公共卫生等方面也比较弱势。尤其是如果遇到经济和战争的危难,在生存压力面前,文化的发展也就常常萎缩。
驯化权力再次。应该说儒学作为一种统治思想,还是对君主有一种约束和感化。皇帝自幼的教育,所接触的文化,还是以儒家的文化为主。但是,官员的权力毕竟还是在君主的权力之下,经常还是无法“用权力抗衡权力”。尤其是在元、明以后,君尊臣卑的情况更加严重。
三
我们还可以回溯到儒学和儒家的形成期,追寻这样一种政治、人文和乡土的关系。
以上第一节所说的是西汉以后渐渐形成的三位一体的格局。在这种格局形成之初和结束之际,都有一次历史的大变局,有一个过渡的时代。这样两个过渡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和20世纪。春秋是儒家和儒学的形成期,回溯到这个时期以及随后的战国,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儒学的地位和使命。
从时代的主要活跃力量来看,战国时代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游士的时代”。它一方面是“士无定主”,另一方面则常常是“游者主事”。游士的特点是“无根”,他们本来就大多是最下层的贵族和平民,没有多少家产和地产。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有机会,有时甚至是很大的机会,但却没有富有的经济基础和世家遗产,甚至没有固定的名位和权力。
而从儒家和儒学形成的春秋晚期来看,儒家是以学为本,以学起家。无学无以名儒。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学招生,五十方周游列国,晚年还是回归学术。到战国虽然各国的统治者求才若渴,但主要还是求能贡献富强之策的人才。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受业子思之门人”的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与上述的法家、兵家、纵横家所受到的重用相比,儒家士人其实是受到冷落的,甚至连阴阳家也不如。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但却“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而一些本来是从儒家之学的热心求功用的士人也纷纷脱离儒家,转而走向法家,甚至包括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韩非,他也曾“与李斯俱事荀卿”,后创立系统的法家学说。至于李斯,则更直接投奔秦国。秦国的强大就得力于商鞅和李斯两位游士,商鞅奠定了秦国富强的根基,李斯则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的大业。但他们的个人命运却都是悲剧性的。而儒家在战国时代,尤其是战火大炽的时期,实际是处在一个潜伏期。
儒学和倡导暴力无缘。我们可以想见那时有道义的儒家士人面对的战乱天下和他们的感受。但儒家的思想还是正大中和,宅于仁心,虽然有时可能缓不济急,但终究是长治久安之道。战国扫荡了世袭的贵族制,秦朝建立了统一的郡县和官僚制度。汉朝在初期实行了一段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之后,终于选择了儒学为其指导的思想。而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与其说是“秦制”,不如说是吸纳了孔子和儒家发扬光大的“周文”的“汉制”。这一“汉制”的重心就是从察举发展到科举的古代选举制度。
四
但是,经过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动荡和洗礼,目前服膺儒家的人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呢?上述那种传统的三位一体、儒家士人一身而兼三任的社会格局几乎可以说是荡然无存了。从制度上看,儒家学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客观处境是“上失其途”“下失其土”。
过去传统儒家士人一身而兼三任的社会处境是有其历史条件的,在政治上是君主制和官僚制;在文化上是一种指向道德修养和仁政的人文文化;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是一种农业文明。现在君主制是废除了,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也大大弱化了,但作为一种“千年传统”还是有其根植于社会深层的生命力。社会经济和技术则由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
不过,今天的社会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还有周文和汉制的“千年传统”的长久浸润和影响,儒学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层面也还是继续发生着影响,比如重视教育和亲亲人伦。但是,社会也同样受到了启蒙和革命的“百年传统”的影响,受到了全球和市场的“十年传统”的影响。这后面的两种影响可以说超过了前一种影响,甚至在文化人中更甚。
当然,儒学并没有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消亡,儒家也没有随着君主制的废除而消亡。如果儒家和儒学就是紧密依附于政治的一种学说和学派,大概就免不了这样一种消亡的命运。但儒学却并不是这样一种学问。它在从事于它的政治实践之前就已经产生,它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兴亡的王朝和政治分裂的时代而不灭,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它常常还是完好如初,甚至在经历了诸多挑战之后更加发展了。
在百年受压之后,近四十多年,在一种相对和平、外无战争、内无运动的环境中,儒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在学术方面有许多的收获,信仰者也渐渐增多。首先在观照其他文明、吸收新知的情况下,对儒学有了多方面的深入阐释,而且也有了一些创造性的阐发。儒学的确开始有了一个复兴,当然也还只是一个尽量恢复的复兴。儒学开始受到了政府的重视,也聚集了一批以现代的新知识和新方法研究儒学的学者,以及一批不仅研究、也是信仰儒学的学者。这两批学者自然有重合,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回到比较原始的儒家教旨和方法的思想者,包括民间,也出现了一些重新服膺儒家的人士。
五
正如前述,儒学之所以在西汉被选择成为主导的思想,是和它本身的性质有关。秦朝是靠法家思想打天下和统一中国的,但最后西汉的统治者还是选择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基本没有改变,且并非“儒表法里”的状况。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的社会,包括平民百姓的心里。这说明了儒学不仅鼓励个人向善,在政治上也是一种适合长治久安的思想。近代以来,中华传统遇到全面的挑战,儒家思想遭到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和“评说儒法”运动中达到顶峰。但是,经过这一切,儒家思想在近四十多年还是有蓬勃的发展,说明了儒学本身即有强大的生命力。
儒学在现时代虽然不容易看到成为主导的前景,但它的确还是大有可为的。儒学的性质在政治方面是具有相对保守的性格的,它可以成为社会的一个稳定器。而儒家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并不是为维护而维护,而是在后面有一种强有力的价值诉求的,那就是不忍“生灵涂炭”,保全生命的原则的。它维护生命和人格的平等,为民制产,不与民争利,保障百姓的小康,但又不主张无限制的满足物欲,而是主张节制,适可而止。它希望人们能够在日用人伦和人生理想上重视精神和文化生活。尤其在个人修身方面,它是积极鼓励人向上的,一种希圣希贤的理想可以让个人安身立命,也为社会奠定一种德性的基础。它不主张一味追求“进步”,尤其是那种单一方向的“进步”。它的历史观和宇宙观从根底上说是天道往还,循环反复的。它还考虑到平衡,而比平等更重要的是平衡。它深谙人性,不仅人的共同性,也包括人的差别性,不对全社会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不提出乌托邦的社会理想。
儒家的哲学有时被讥为“道德常识”。我倒是希望为儒学的常识性质辩护。它是一种生活的常识,道德的常识,甚至连叙述也保持平常。而验之于当代西方学界各种层出不穷、新奇可怪的理论,包括一些忘记了常识,甚至扭曲常识的理论,倒是让我们感到从古到今的一些基本常识的可贵。
儒家之注重常识,可以用后来成为几百年科举考试指南和文本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认为,儒家其所以为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谈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圣人“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而“道”并不是深不可测。他引孔子之言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道不远人”,他解释说:“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儒学不必高标高蹈,孔子的学问本来就是平实和亲切的。无论如何,儒家学者如何守住学脉,以及这学脉后面的道脉,这方面还是可以从儒学创始者的孔子那里得到宝贵的启示。
当然,当代儒学还需要面对新的挑战。过去的中国是一个乡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乡村为基础的社会,文明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文明。但是,今天的中国显然也进入到了一个以城市为重心的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工业文明乃至高科技文明之中。儒学如何从自己的古老智慧中吸取对现代文明的应对之方,也为世界带来思想的借鉴,还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探索。儒学还会保持人文的基本特色,除了开拓道德形而上学和发展政治哲学之外,还可以深入到各个具体的领域,诸如伦理、法律、科技、乡村建设和城市治理等等,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做出自己的回应和思想贡献。
责任编辑:近复
作者文集更多
- 【何怀宏】君子的人格 12-29
- 【何怀宏 赵占居】将无同?岂无异?——··· 06-07
- 【何怀宏】我们想要怎样的人类文明? 08-11
- 【何怀宏】政治、人文与乡土 ——当代儒··· 07-06
- 【何怀宏】人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伦理道德··· 08-08
- 【何怀宏】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 10-28
- 【何怀宏】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 07-27
- 【何怀宏】抗议性政治不应成为主流 07-13
- 【新书】何怀宏:谈成功的书多,谈生··· 03-30
- 何怀宏著《新纲常》出版 11-19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