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出版暨各卷前言
《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出版暨各卷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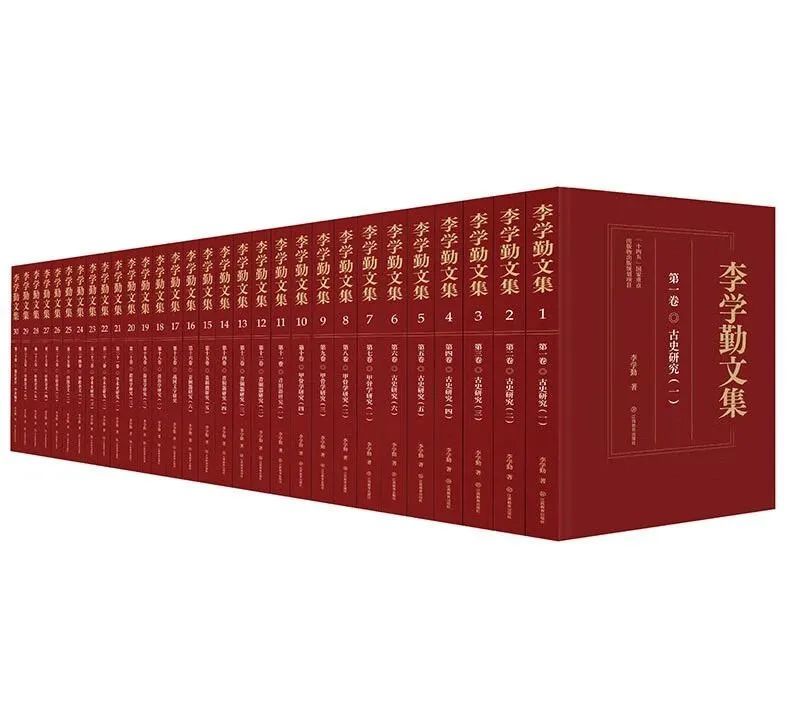
书名:《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
作者:李学勤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内容简介】
《李学勤文集》收录了李学勤先生自1956年至2018年期间所撰写的中文论著,分为7大类,古史研究(附文明起源研究,共6册)、甲骨学研究(附文字起源研究,共4册)、青铜器研究(附铜镜研究,共6册)、战国文字研究(附古文字学通论,共1册)、简帛学研究(共3册)、学术史研究(附国际汉学研究,共3册)、序跋杂文(共6册)。全套文集共30册,最后一册为目录和索引。每一大类中先收专著,再收论文。文集总字数约1000万字,30卷。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大类的最前面,李先生生前都专门口授完成了一篇“前言”,讲述自己的研究体会。该文集的编辑体例也是由李先生在病中亲自拟定。为体现历史的原貌,除修正个别排印错误和为符合国家出版规范所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外,收入文集中的论著均一仍其旧。
【作者简介】
-9.jpg!article_800_auto)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兼多所大学教授。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6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资深教授。研究领域为先秦史、古文字学和文献学。出版著作40余种,论文2000余篇。
【各卷前言】
《古史研究》卷前言
首先当然非常感谢出版这部书的江西教育出版社,他们毅然接受了出版这样内容庞杂又比较冷僻的论文集,这是很不容易完成的一项工作。
其次要感谢参加本套文集编选工作的几位同人。由于这些文稿的写作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有很多内容我本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加之这些文章发表的地方各式各样,很多材料寻找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特别感谢这几位同人为搜集各篇论文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广泛,又因为工作关系从事过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我把这部论文集分成了七卷。在每一卷的前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目前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也可能有一点儿参考价值,并借此机会回答朋友们对我的一些问讯。
我记得1971年的春天,我们中国历史研究所搞运动,下“五七”干校,当时在河南明港的“运动”已经松弛下来,有些考虑学术问题的时间了。一天晚上,我和应永深先生一起在星空下散步,他忽然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搞了这么多年先秦的研究,将来的目的是不是要写一部先秦史的书?”我当时就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考虑过,所以也就没有回答。可是后来,我屡次回忆起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甲骨文、金文等等都和古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研究一个学术的分支学科,比如就古代史范围来说,那就和几个学科有关系,除了狭义的历史学,还有中国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等,都和大的基本目标有关系。那我我们应该从中怎么选择、抓问题呢?这又使我想起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侯外庐先生,他曾经特别跟我讲过“你不要老想做那些很具体的事儿”,尤其是他强调“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这句话当时使我十分震动。70年代,我回想到侯先生这句话,就是我们做一些工作,都要联系到一个大的、有理论性的目标。
对于古代史而言,也是一样的。做古代史研究,当然要依靠和联系那些分支学科,而做分支学科的学者也不可能去做全面的古代史研究。可是,整个的历史研究、古代史研究,是在很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这就要求几个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分支学科的研究要关注历史方面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慢慢我就想到了要写那篇《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章。1981年,我参加了徐中舒先生在西北大学组织的第二次先秦史讨论会,当时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我讨论的问题都是从那里推衍出来的。
我不是说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问题都要是理论性的,但是要与理论性的大背景相结合。当然,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比方说,我们考释甲骨文,认出一个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整个的工作、研究的背景应该侧重于与理论有关系的问题。我多年以来特别想把侯外庐先生那段重要的话告诉大家,这次有机会了,我觉得很高兴。
李学勤
2018年3月26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甲骨学研究》卷前言
这里我想谈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很多朋友对我当年研究甲骨文充满了好奇,猜想我有家学渊源,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师传,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虽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可是我的父亲并没有教过我任何有关甲骨文的知识,他也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那么,我是怎么接触到甲骨文的呢?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上高小的时候,住在北京朝阳门南小街附近。我有一个同学姓常,他跟我关系很好。他的父亲是北京贝满女中的老师。有一次,这个同学告诉我,他父亲对他说,中国的学问是非常多的,可是最难的是甲骨文。我听了这话就很用心,开始留意甲骨文方面的知识。因为我有个特点,越难的东西越想学,越不懂的东西越想懂,而且特别喜欢那些带有神秘性的东西。刚开始时我光记得“甲骨文”那三个字,可是不知道什么是甲骨文,甚至于在马路上看见有碎的石碑,我以为就能找着甲骨文了。这是我念高小时的事情。
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可以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了。一翻北京图书馆那个卡片柜,才知道有那么多甲骨文的材料,于是开始接触和学习甲骨文这门艰难的学科,这一做就做了半个多世纪。
所以,这是一个小男孩自己闯进甲骨文殿堂的故事。
下面我想说一下什么是甲骨文。
现在我们对甲骨文的定义在很多方面要作一定的修改。通行的说法,甲骨文是商代盘庚迁殷以后殷商王室用来占卜的记录,出土地点在安阳殷墟。用以占卜的材料——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是用当地的乌龟和牛骨加工而成。一直到现在,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可是仔细推敲起来,其中每一个论述又都存在一些问题。
甲骨所用的动物骨头不只是牛,还有其他动物,比方说鹿,甚至于有人说还有大象。而所用的龟甲兽骨也不都是当地的,有些龟的产地居然是在南方,甚至是在今天中国的境外地区。
甲骨文内容也不都是王的,殷墟就有非王卜辞,这个观点是大家都接受的。
另外,甲骨不仅商代有,西周也有。西周的甲骨最早出于山西洪洞,一直到最近山东的高青,特别是周原和周公庙,发现有较多西周甲骨。因此,甲骨不只是殷商那段时间的。
当然上面这些甲骨都是较个别的,除了西周甲骨数量比较多之外,其他数量都极有限。可是能够有这些线索,就意味着将来不是不可能突破。
李学勤
2018年3月1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青铜器研究》卷前言
在《甲骨学研究》卷的前言里我说了我学甲骨文的经过,下面我想说一下我学青铜器有什么样的故事。
大家看我的经历可以知道,我接触青铜器也同样不是很容易的。每次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三代吉金文存》或者《小校经阁金文拓本》,都是很需要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的。实际上,在1956年我已经把《殷代地理简论》的稿子做好了,本来可以很快出版,可是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这样到了1959年才出版。
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思想上的错误。这错误可以用孔子的话说是“画”,就是自己限制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自满的情绪。为什么呢?比方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和一个同事谈话。那同事说,你甲骨文还要学习什么,甲骨文还要研究什么。我说,甲骨文也就这么多东西,也没有多少。这就是一种自满的话——其实,对于甲骨文,就到今天,我也没懂多少——这是很要不得的。所以,当时我也觉着好像我懂了青铜器的铭文,实际上不是这样子,青铜器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好在我这个人还是有一个自己检讨的习惯,很快我就察觉出自己有错误。因为当时发现几件重要的青铜器,比如禹鼎,我就没有能力去真正做什么研究。这就说明我自己能力是很差的。我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所以我就找机会去看有关青铜器的书。我的计划是,就如同我学甲骨文一样,一种一种地看,各依次序,从宋朝看起,一本本看下去。可是那时候要搞运动,还要完成所里交给的工作任务,没有时间,所以我在青铜器方面做的也不多,好在后来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参加修订《中国史稿》。我是1970年10月下“五七”干校的,到1971年冬天,郭老(郭沫若先生)把尹达先生等几个人,包括我,调回北京,参加修订历史所编的《中国史稿》。那时候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有空的时候我就看所里的书,就好像那个图书馆是我一个人用一样,和青铜器有关的材料随手可得。当时我就立了一个办法,就是按照考古的时间次序来排列,从宋朝看起,一直到民国。研究也是尽可能按照青铜器的时代和发表的次序。我觉得读青铜器的书,应该更能看出青铜器的研究是和考古学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愿意贡献给年轻读者。
我们学青铜器,和其他许多考古遗物一样,要多做分域、分期的工作。在青铜器方面来说,分域是最主要的。我最近这几年有个想法,想什么时候能够编一个中原地区的分域表。我说的中原地区是狭义的,主要指以西周王朝为中心,和后来中原的几个国家,特别是西周的,主要是宗周、成周和附近的几个诸侯,甚至于连晋国也要区别开来,因为晋国受戎狄的影响太深,《左传》桓公二年说:“晋,甸侯也。”当然它可以算中原地区的一部分,但像郑国才是比较合适。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
而从现在来说,把一些青铜器进一步根据相关材料排排队,是很值得的。当前西周里面比较好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很快就要出版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历谱集中了很多学者的力量,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有些不同意见。我参加这个历谱的工作,也觉得里面确实还有些问题,问题主要在于西周中期。从西周晚期往上推,推着推着历谱就断了;而从上往下推,有些地方又是连不上。所以,做好西周中期的整理是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好在最近这方面材料比较多,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工作推进一步?不知道我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
近些年,青铜器研究的发展真是非常迅速,让人有赶不上的感觉,至少现在的发现和研究都是这样快地发展。我想特别提到的是,过去大家认为不重要的铜镜,正在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羽毛丰满的青铜器分支学科。你可以说它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部分,可是它有它的特点。所以关于铜镜,我在编这个集子的时候,建议把一些小稿子分别排列。不过,铜镜的研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尽量发挥考古学方法和研究的作用。因为铜镜器物特殊,数量很多,到处都有,而且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当然有许多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可是大家却了解得相当少,比方汉镜、唐镜,每一座墓葬出土能有两三面就已经很不错,一般就一面,有的根本就没有。很好的墓葬没有镜子,因为不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每拿到一面汉镜,就有可能意味着又发掘了一座汉墓。可是怎么会有那么多汉墓?这个问题就摆在大家面前了。
我过去讨论带钩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件带钩虽小,却可能体现出当时最高、最复杂的工艺技术。铜镜情况也是这样。有的铜镜非常大,如临淄出土的大长方形铜镜,有一人那么高,可是工艺比较简单。有的铜镜很小,却集中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技术,例如90年代初期我在欧洲看见过一面很小的平缘镜。这个铜镜的直径不到10厘米,却十分精致,镜背有朱、墨两色漆绘的花纹,有楚人的风格。镜子外面套着一个柔软的皮制镜囊,现在还存在。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镜囊上也画有一个图案,和镜背的图案竟然完全一样。可以想象,这面铜镜过去是佩带在人身上的,佩带的人很可能是一位南国的佳丽。
李学勤
2018年3月13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
关注我的工作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大家都说我的工作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确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做甲骨文的。可是,可能有人会发现,我在历史研究所内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或者后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都不是关于甲骨文,而是关于战国文字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要回忆到我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的时代。
当时要查一些青铜器、金文或者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要看这样几部书。一个就是《三代吉金文存》,如果借不到,碰巧被别人借走了,那就要借邹安的《周金文存》,或者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后面这两部书里战国时代的资料很多,而且大部分附有当时做的释文。我就借来看看,本来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随便翻翻,可是越翻越觉得他们做的释文特别不对,错误太多,这是当时的情况。当然读他们的释文也有不少收获,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我就想,如果我来做,也许可以给他们做一点补充。当时做这项工作的人有邹安、褚德彝等等。从那时起,我对战国文字就有点注意了。这就是我走进战国文字的一个原因。
当时随便翻翻的收获是很大的。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战国时代列国的不同文字,正如许慎所说,是“文字异形”。这一点虽然有人指出过,可是没有成为一个系统。我经过几年的工夫,慢慢体会到,中原地区三晋、两周(指东西周)的文字,基本属于一个类型(后来又包括了中山国,这是因为中山国曾经被魏国占领)。这样,中原地区就以三晋文字为代表,成为一类。另外,秦国文字,如王国维先生特别强调的,有西土文字的特点,当然是一类。然后,燕、齐、楚国的文字,又各自成为一类。若找着一个文字在几个列国的不同写法,把它们排列起来,几个系列的特征就很明显地展现出来了。有关五个系列的问题我在《战国题铭概述》等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最近这几年我有一个想法。因为这几个国家里没有战国时代很重要的吴国和越国,有没有可能吴越文字可以单成一个系列?那样的话,战国文字就不是五个系,而是六系了。这个想法我在《〈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前言》等个别文章里曾经提到过,可是后来我又收回了。因为奇怪的是,特别是越国,虽然一度很强大,甚至到后来北上中原,而它的文字材料却很少。不是没有,比方说有越国的编钟,铭文很长;可是有文字的一般器物,特别是玺印、钱币这一类,越国却是一件也没有发现。难道越国人不花钱吗?越国人不用玺印,不进行商业活动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怎么回事,至今还是个谜。常常有人找我,说他发现了越国的货币或者越国的什么,都不可信,所以第六系还是先收起来。这一点是我要向读者说明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我早期写的一篇关于战国文字的文章,引了一些玺印,还有个别其他东西,实际上是假的,在当时却风行一时。其中最有名的是将渠玺,清末民初很多有名的学者都承认这方大玺印。据我所知,当时只有王献唐先生指出它是伪玺,这在我的文章里曾说明过。此外,还有一钮端方的大玺,就更不用说了。20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在京都的滕井有邻馆见到了这两钮大玺。仔细观察后,知道都是假的,特别是端方的那个玺印背面还镌刻了许多蝌蚪形状。这也在我的文章里提到过。
谈到玺印,还有一种文字需要在这里说一下。在中国古代,至少还有很重要的一类文字,至今未能得到很好地解读。其时代也主要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那就是所谓的巴蜀文字。巴蜀文字一直是很大的一个谜,却很重要。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看见一本苏联的科学杂志,上面有一个专栏,谈到世界上没有解读的古文字还有五六种,谁能够解读一种古文字,那就是科学上的大发现。这个由于那个时候(1952年)英国的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刚刚解读了希腊的线形文字B,所以大家都很热心做这事。
李学勤
2018年3月17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简帛学研究》卷前言
我想在这里借机会提个要求,凡是看我这套书的读者,能不能帮我宣传一下。首先,就是中国古代的竹简以及木简,不是像有的电视剧里面所演的那个样子,又厚又重,好像是短短的竹木板用绳子捆起来一样。我们的祖先不是那么愚笨的。实际上,就拿真的竹简来说,最长可以长到50厘米,宽也只有半厘米左右,用丝线编联起来,非常玲珑秀气。当然这点我不要求做电视剧的人一定要这样做,但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其次,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竹木简上的字是用刀刻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竹木简是不能刻的,一刻就会坏。而且谁会用刀在简上来刻写文字?这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所有竹简、木简以及帛书上的文字都是用笔写出来的。古人有笔,有墨。战国时代的笔和墨,在考古工作中都已经有实物发现。我们所看到的笔、墨实物非常玲珑小巧,有的笔上还有笔套,可以用手来推动,能把笔很容易地取出来。墨和砚台那时也都是存在的,并不比汉代的差多少。
这里附带说一下,还有些人认为,古代有一种漆书。“漆书”一词,确实见于古书。可是中国的漆是不能真正用来书写文字的,那写出字来又大又笨。因为漆是很粘稠的,不可能用来作为一般的书写原料。所谓漆,实际上是黑色的意思,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讨论过,我在这儿就不详细说了。
还有一件事,关于清华简。清华简的整理与保护工作,到现在已经进行整整十年了。我们十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有一点,我特别想在这里强调一下,那就是在清华简整理中,拍照很重要。清华简入藏以后,经过清理,到2008年10月,我们请各方面专家开了一个鉴定会。这会上,有学者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那就是要尽快、尽可能地拍好彩色的照片,不但要有正面的,而且要有反面的,一定要原色、原大。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大家知道,像竹简这样的文物,是很难保存的。不管我们用多大力量来保护,它们总会多少有些变化。正是这样,我们要力图把它原始形态保存下来,把一些我们看到的现象保存下来,这必须有好的摄影,是很不容易做的事。这个问题在我这部书里有几处都强调过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想法:还需要很好拍照的、还需要很好做记录的简帛文物,希望发现者都能够尽快地做出来。
现在我觉得有两件事我们要做好准备。
第一件事比较简单,那就是要准备好再发现早期的帛书。简帛的帛是很难保存的。迄今为止,古代的帛书只发现过两次。一次是1942年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帛是放在一个竹制的篮子里;第二次是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帛是放在一个盒子里。这两者的保存都有些遗憾,特别是子弹库的帛书损坏更为厉害。所以,对于以后我们还可能发现的帛书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样去抢救,都应该有一个规范的过程。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一定要避免一些像过去发现时造成的损失。
再有一件事,是我们要准备好在中原地区,甚至很北的地方,有可能发现竹简。因为当时竹简是普遍使用的,在北方同样有竹简,只是保存不好就是了。我们看著名的西晋的汲冢竹书,就是干的。因为当时发现的人据说曾经到墓里去拿着竹简点火照明,这就可见简是干的。还有,近年在山东临沂发现的银雀山竹简,并不是干的。所以,即使在北方,发现干的或者不干的竹简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我们要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在中原墓葬发掘的时候,这个工作很重要,以免损失重要的材料。
李学勤
2018年3月22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学术史研究》卷前言
有学术就必须有学术史,这个道理我在书里已经多次讲过。我们读一部重要的书,应该考虑到它在学术史上的位置。
在学术史上重要的书,是不可不读的,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读不了多少书。我小时候总是幻想尽读天下重要的书籍,这当然完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一种书也读不好。要深入地读好一种书,要做很长时间、很深入的工作。比如,我这几十年以来一直想读好朱子的书。朱子是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学者,当然我们怎么评价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的重要性是明摆着的。我有好几次想好好读一下朱子的书。早在1946年前后,在北平(北京)出版了一部李相显写的《朱子哲学》,我当时有这套书,一直想看,可是却没有时间好好去读。我到历史研究所,本来研究思想通史,正好有机会看看朱子的书,可是朱子的书太多,要求时间太紧,也不可能看得很仔细。后来编《宋明哲学史》,我就没能参加工作。到近年,我又看到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这几部书我都保存了很久,可是都没有时间去读。一个人的著作都读不好,何况中外古今?要想尽读天下书籍,当然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曾有人问我,假如我还有时间和精力做一点工作的话,想做的事儿是什么?这当然不是指的我现在正在做的清华简。清华简研究的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在清华简之外也实际上做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作为一种设想,我说,如果我有时间和能力,那么我要再写一本《殷代地理简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殷代地理简论》的基本思想是在修正了的分期基础上,用历史地理的方法来贯串甲骨文,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还是可取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做这个工作。因为,甲骨分期现在还有可以修改之处,特别是最近发现了所谓无名组晚期和黄组还有重叠的地方,这样影响是很大的。可见,我们在分期上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讨论,这当然可能不是我能做的事了。
李学勤
2018年3月24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序跋杂文》卷前言
我曾经笑说,我可能是近年写序跋写得最多的人,所以,在做这一《序跋杂文》卷前言的时候我本应该多说几句话。
写序跋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序跋使我读了更多的书,看了更多的文章。有些书虽然我一时看不了,部头太大,或者内容跟我的知识无关,可是,我看这些书,至少看了绪论和结论部分,并从中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今天我常常说我是“杂学”。之所以杂,其实这也是一个方面。应该说,写序跋是我和学术界联络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大家面前会有这么多序跋。如今,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这个事。所以,在这里我想做一个郑重的声明:
从今以后,除了直接做的工作以外,不再写任何序跋了,我要把我剩下的精力和时间都注入清华简和中心的其他工作上来。这样,或者我可以多做一点儿贡献。
我这样做,其实对我个人是有损失的。因为这样,有很多的学术内容我就不能够接触了。希望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向大家请教吧。
李学勤
2018年4月5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前言
写到这里,已经到了这部文集的最后了。在这部文集最后还要不要写前言,我一直在犹豫着,不知道应该怎么写。因为自己的工作离着“已完”还远得很,没有一个终了。整个的研究工作就好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这样我怎么能说事情已经做完了?可是,我个人在自己小小的能力之下,在研究工作的长河中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终了。编一部文集,也算是一个终了吧。当然,这不是说我工作的终了,只要我还有精力,还有能力,我还要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当前最需要做的是综合工作。有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或者已经有些线索了,可是没有把这些综合起来考察,提出若干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想这一点,应该在我这部集子“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说一下。
我还想说明一点。我常常说自己是“杂学”,杂学含有多的意思,就是都想学,什么学问都有,什么也做得不透。可是每一项的整理出版不但是自己的、助手的或者朋友的工作,而且也是出版社的、编辑朋友的工作。所以,我想在文集的最后感谢出版这部书的编委和出版社。
负责编辑文集的几位同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此次找到了很多我早已遗忘的,或者是我都想不到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把它们编在一起,并且做了索引和编年,这些工作非常烦杂,非常“可厌”。用“可厌”这个词来形容并没有过分。所以,编辑的工作实在是太主动了,由几位学者来做,也实在是难为他们了。
需要特别感谢编委的还有一点,就是修正了一些原来明显的错误,这些改正多数没有注出,可是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这也是编委所做的重要贡献。我常常说,任何一项科研工作的最后,都要表现成报告或者成果,编辑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要感谢编委的工作。
还要感谢的是出版社。整个的科学研究工作都以出版社为最后的出口,没有出版社,就没有研究工作,或者研究成果就不能保存下去。出版社做得越好,这项工作就表现得越好。我希望学者同事们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和编辑朋友们更好地合作,更好地联合,把工作做好。
这些是我编到这个时候想到的几句话。总的思想就是对编辑和各位朋友表示感谢,特别感谢那些出我这部杂七杂八书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李学勤
2018年5月3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责任编辑:近复
【上一篇】落笔书院2023年第二十期读书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