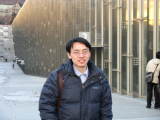
【许家星】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庸》解的评议为中心
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黄玉顺】《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
《易经》之“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易经》之“帝”亦然,与“天”同义,同位同格。《易经》“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易经》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

【廖可斌】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贾泉林】章太炎晚年儒学诠释的三种面向
章太炎晚年“粹然成为儒宗”,积极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学,其对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诠释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具体可以总结为三种面向:一是历史的面向,即从奠定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角度,肯定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历史合法性;一是世界的面向,即在中外文化、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中,确认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构成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

【邓秉元】易象与时间——关于易象学的论纲
本文首先基于相论视角,区分了人类知识体系中几种对现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从熊十力、海德格尔两条线索追问出德性易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进而通过《周易》卦序的诠解揭示出易象学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学对传统中国学术的奠基意义。论文最后从易象学角度初步探讨了时间的意义以及历史本身的先天结构,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历史···

【杨泽波】再议“善相” ——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周广友】从“本一”到“合一”:重思王夫之的天人关系论
通过阐释张载的本一论与合一论,王船山辩证地考察了天人之间的分合异同关系,其论析蕴含着未分-分-合的时间维度和逻辑环节,包含有事实与价值、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等不同识度,体现出船山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辩证思维和既以人合天又以天合人的中道思维。他所区分出的天之天、人之天、物之天等既新颖别致又意涵丰富。他提出要“以天···

【周磊】孟荀之间:罗钦顺思想的内在张力
在人性论上,从“理即气之理”的原则出发,罗钦顺对“气与性一物”与“性即理”均持赞同态度。以阶段性论性,意味着孟子性善论适用于一气浑沦的理一阶段,荀子性恶论对应于成形之后的分殊阶段。因成形不可避免,故应就着现实的人性为善去恶,“复性”模式被摒弃。
.png!cover_160_120)
【黄玉顺】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
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博爱)与“礼”(制度)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意味着“礼”是“仁”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因此,从管仲“不知礼”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礼”。

【黄玉顺】论自由与正义——孔子自由观及其正义论基础
孔子具有自己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境界论的自由观,而是人性论的自由观。“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是这种自由观的主体性维度,即个体主体具有天然的自由意志;“正义的社会规范”(礼)是这种自由观的规范性维度,即它是以孔子的正义论为基础的。

【李景林】道与学——孟子圣道传承论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传道”之义,肇端自孔子,孟子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圣道传承论。此圣道传承,包括“道”“学”两面的统一。在传道的谱系中,“闻而知之”的圣人,以内在性的倾听独知天道,凸显了“道”的超越性意义;“见而知之”的贤人,将圣人得自于天的创作落实为制度典常,凸显了“道”的实践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

【杨国荣】中国哲学中的心、性、情
从内在的结构看,心、情、性融合于心,所谓“心统性情”,便侧重于三者的内在关联;就心、情、性本身的起源与衍化而言,其变迁又关乎性命之学。“天命之谓性”以天之所命的形上形式规定了意识的内在可能,那么,兼含必然与偶然的“命”,则构成了成性或成心(意识和精神形态的发展)工夫展开的多样条件。以“命”为根据和条件的工夫过程,最终···

【孙海燕】明明直照吾家路——思想史上的《近思录》系列之五
从人性发展看,孔子的“成圣”之道,展现为一个由生理、情感、理性,再到觉性的自然流程,道德理性(非觉性)又是此流程中的关键之关键。这里所谓的“道德理性”,主要指理性层面的伦理需求,是依靠“仁义”的力量“修己以安人”。该理性的特色,在于其有着浓重的情感因素,它统摄了情与理、利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人性侧面,构成了一复杂的···

【何青翰】工夫与教化——论朱子“学之大小”思想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与“学之大小”的思想结构相应,朱子在工夫上先后将“大学”“小学”分判为“格物”与“主敬”;与此同时,朱子编撰《小学》,注释、序定《大学》,重塑了以“小学”“大学”为基础的教化体系:以“礼乐射御书数”入“小学”,以“大人之学”阐释“大学”,强调了人皆可以“学为圣人”的平等性,又构建了高下有分的德性秩序。

【刘强】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认同。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

【李佳】儒户、生员与元明社会管理模式变迁——以基层儒士优免为中心
元明易代后,元代实行的儒户制度与生员制度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

【刘强】《世说新语》“名教乐地”说新解——兼论西晋玄学家乐广的玄学立场及思想史意义
乐广此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是对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辨”的现实回应,从中可见乐广在“贵无”与“崇有”的二极论争中,秉持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中道立场,体现了他对儒家“名教”中“内圣”境界的体认和捍卫;另一方面,此说还直接启发了宋儒对“孔颜乐处”的探寻,丰富并提升了宋明理学中“名教之乐”的思辨品格和形上···

【黄玉顺】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 ——《诗经》美学思想研究
《诗经》出现大量的“美”字,并且不再与“善”相关联,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好”来统摄。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诗经》所有“美”字都形容人,包括女性之美和男性之美,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而是“人的美学”。

【孟鑫】简述“文”在汉语世界的多元意涵及其对中国阐释学理论建构的价值
现代语境中的“文”,往往指向文字、词句、文章、文本等固定领域,而在历代汉语文献的考察中,‘文’则体现出剥离语言文字、文章、文本的固定领域,而向着中国社会基础层面延伸的显化状态,并最终形成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导向意义的“文教”传统。

【乔飞】作为儒家法律思想基础的“天”
“物质自然之天”“神灵主宰之天”“义理规则之天”可以整合为“位格之天”,荀子、朱子以及王阳明对“天”的理解皆莫出其右。“位格之天”显明了“天”的生命属性、伦理属性以及至高、永恒等属性,其不仅创生了万物与人类,还对万物和人类拥有主权;权力的来源、法律的创制、司法的过程等儒家法律思想核心问题,无不与“天”有关。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