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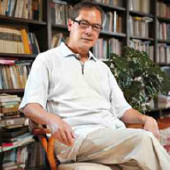 |
何怀宏作者简介:何怀宏,男,西历一九五四年生,江西樟树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道德·上帝与人》,《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等。 |
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
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共识网
发布时间:2012-06-25
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
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或者说,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标准或自我要求。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或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
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是“独立”而不是别的什么,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独立当然不是指完全在客观上独立,脱离社会而孤立,而是说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此行,一旦从事观念性的工作,就应当有一种思想和精神上要尽量独立这样的自我意识和要求,并且努力为自己创造保障这种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独立是第一步。独立不是最高的要求,而是基本的要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可能是最高的要求--如果这种独立性的条件被从外部几乎剥夺殆尽。在独立思考之后,知识分子们的观点仍会呈现为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倾向,也许他们掌握的还都是片断的真理,包括一些具有某种时代或历史意义的真理性认识,但是,这种观点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却是所有这些观点的共性。“独立”也就构成所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本色”或者说“底色”。
独立于什么?怎样才算是独立?如何保持独立?我想知识分子应当首先独立于权力;知识分子也应当独立于金钱;最后,知识分子还应当独立于大众。“独立”主要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但就像自尊也需要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也需要有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如果知识分子不断被软硬兼施地打击、摧残;如果他们连自己人身安全和物质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即便他们独立意识再强,也很难说有一种独立,或者说只可能有极少数人的悲剧英雄式的独立。而这种独立的社会条件又不能说是等待而来的,恩赐而来的,于是这种“独立性”还包括对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独立性有明确的自我认识和要求,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要为此有实际的努力斗争和争取。
独立性包括取得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这在我们要独立于权力时往往是特别需要的客观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以经济利益为自己的主要追求,也就是说不仅客观上要争取经济自立,主观上也要独立于金钱。他们要能够在经济上生存,而且可能的话,还有还要争取一种经济上体面的生活。虽然“何为体面生活”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差异,不同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经济独立”也会因人而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自己的挣钱能力或遗产获得一种不错的独立性,而有些知识分子则可能通过自己的生活简单和淡泊同样获得自己的一种经济独立性。但总的说,起码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价值追求都是需要的,而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与他们物质上所求不多或者价值上别有所求也有相当关系。
保持独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在客观世界争取能够保障自己的独立性的东西,首先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如果可以用笔耕养活自己,使谋生和观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实在不能,也能用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另外,争取独立还包括争取观念产生和传播的自由空间,甚至如果能够自然而然地有一些名望和影响的权力也不刻意拒绝。另一个方面是在内心世界降低欲望,不以追求财富或权钱名为自己的目的,对物质的生活适可而止,甚至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真理承担艰难的物质生活与其他压制和迫害。就像《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理念人应当是为真理而生活,而不是靠真理而生活的。
的确,精神独立最重要的根源和动力也还在精神,这种精神淡化我们的物欲,将一种更高的追求放在我们面前。知识分子要独立,首先他自己在精神人格上要站起来而不趴下,就像他要获得社会的尊重,他自己首先要自尊自信自强而不自贬自污自辱一样。当然,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他应当努力以自己的独立精神来扩大自己的独立空间,同时又准备即便受限受压也要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独立并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尤其在社会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但有时也会成为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时会有权力、金钱、大众中的两者结盟、甚至三者结盟的情况,这时的“士”(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就不仅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而且要“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一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主张,大概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最直接的来源可以说是来自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我在这里只是想强调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涵义的第一性,强调它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标准。亦即,是“独立”,而非“批判”、或者“公共”、“普遍”等其他标准,是我们辨认知识分子的首要标志。这种独立在我们这里也并不是已经实现的状态,而还是有待于努力奋斗去争取的目标。
这一“独立”标准在现当代西方知识分子那里似乎不是太被强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那样一种“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过程,没有处过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处过的那样一种长期压抑和受迫害的状态。或者说,他们感受不到多少硬性的来自权力的强迫和压制,也没有太多危及生存的经济压力,而更多地是感受到来自市场和大众的隐性压抑。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强烈起来的要求中国知识分子重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呼吁,其后面的背景是近百年来他们其实很不独立的历史。更一般的原因或还因为观念的精英是比较自由流动的个人,没有很固定的社会根基而容易依附。知识分子不直接生产和掌握物质资料;他也不掌握可以直接调配这些物质资料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政治权力。这是他们的优点,又是他们的弱点。说是优点,在于这种自由流动的特征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这对观念的自由孕育不致受先定的阶级和阶层立场影响是有利的;说是缺点,则在于他们缺少实际的资源和物质手段,而知识分子毕竟也还希望看到自己的观念被传播、普及和实现,从而因要去寻求实现它们的实际手段而容易依附某种现实力量。
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自由飘游(free-floating)。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而是一个社会中保有相对自由的集团。于是这初看好像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说知识分子是最为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知识分子优先地是要获得自己的独立基础,获得能让自己独立的社会根基,包括获得某种经济基础或物质根基。后者会不会损害前者?强调独立、强调获得自己的结实根基会不会有损他们的自由流动和选择?我理解这里所强调的“独立”是落实于个人的,作为集团,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自由流动的集团,“自由漂移”的含义可解释为知识分子可以参加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者不固定地参加任何一个。而如果他们个人能够独立,恰恰就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这样做--即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真理的“利益”来进行选择。他们最后实际上会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阵营(当然,如果加入了一种强固的政党组织,完全接受了纪律对思想的约束,是否还能算作知识分子就大概要另当别论了),发出相当不同乃至对立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来说没有它自己的特殊物质和经济利益,没有它自身作为整体的阶级利益。但他们可以参与各个阶级阶层,各个阶级阶层或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选择对他们应当说是自由和自愿的,是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结果,而不是政治裹胁和经济压迫的结果。
总之,我们强调独立性是在个人的意义上强调的,这也是“人格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虽然最后可以选择加入到某个集团,成为这个集团最虔诚和热烈献身的一员,但他先决地还是个人本位的。在这个意义上,称他们为“分子”也是有道理的,即他们先天地是个别的“自由分子”而非“组织成员”。
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的著名“皮毛”理论认为,知识分子是“毛”,他们过去依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今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看来最后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否则就将不存。艾思奇也曾经在解放初期形象地比喻说,知识分子就像砖块,要么砌到新社会的墙里,要么就要被扔掉甚至打碎。的确,当新的国家是唯一的雇主,一个政党是唯一的“恩主”和“金主”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几乎不可能保持的。故而只谴责那时的知识分子“软骨”是不公平的。那个年代里,像张中晓几乎可以说是饿死的,而在像夹边沟一类的劳改农场,知识分子更是大批地饿死,文革中则大批地被批斗或者整死。对那种在巨大生存压力和社会压力下的妥协,我们还是要尽力去理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个最严酷的时代,知识分子再要扭曲自己以获取丰厚名利,就不能再逃避“放弃自己的独立性”的指责了。而“皮毛说”也的确使我们从反面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需要社会经济的基础,需要起码的人身安全、物质生计或产权的基本保障。要独立首先要有经济上的独立,这有两种办法,一是自己能够挣到自己的生计乃至体面的生活;一是即便挣不到体面的生活,也能够安贫乐道。但是,即便再压榨自己的生存欲望,一个基本的生计还是不可少的。所以,今天每一个知识分子最好都能自己使自己成为自身的一张结结实实的“皮”,取得经济和人身独立的坚实基础,如此才可望有较充分和广泛的独立自由。一般来说,人只有取得身体生命的某种独立,方能取得精神生命的独立。要让自己的心灵充分自由,不妨先让自己的身体有所安顿。为了自由地思考和自由的流动,必须首先有个人独立的地位。人格的独立是第一步,而经济独立又是人格独立的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或许有人会问,独立自主不是所有人的希望吗,独立自主的个体不尤其还是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普遍要求吗?为什么要特别在知识分子这里强调?我想这大概还是和知识分子的观念工作有关。思想观念的孕育、产生和传播是需要相当自由独立的空间的,而思想还有一种可能冒犯权势或大众的危险。无论是说出一种始则被权力有意掩盖,后又得到大众惰性支持而继续遮蔽的历史真相,或者追求一种自我认定的与主流有别的观念真理,都是要冒有相当大的风险的。所以,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需要一种比其他职业更高的自我要求和力量支持。
知识分子可能是社会结合上最松散或散漫的一种群体,它的成员也最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而且在纷争起来最不容易妥协,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理念、真理,而不是利益、物品。但是,“知识分子”又可能是一种精神联系最紧密的群体,尽管在其内部也互相竞争或排斥,它却也可以使一个人在最遥远的国度或者最预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同道并终身不渝。知识分子不是大众,也不是严密的组织,但他们还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各样的“小众”,当然,也可以非常独立地几乎就是他自己。
尽管“观念的人们”永远会竞争和斗争,但他们最好还是能接受某些基本规则的约束来斗争。而且,所有“观念的人们”最好都能有一种稀薄的群体意识,即他们尽管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也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同一种类的人,即一种和权力精英和大众有别的人,一种“观念的人”。他们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基本权利,尤其至少是言论的自由。甚至他们也许还应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情,即便竞争和斗争,也还是不毁损对方的人格,不因言论观点的对立而要把对方消灭,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道德人格。
这里可以再谈谈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及他们的处境。作为“观念的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处理观念的,是通过处理观念的工作来体现人的特性和影响社会的,但是,这种观念性质的工作在所有人类的工作中居于何种地位呢?它在塑造人类社会和推动社会演进中具有何种力量呢?它一定要是具有某种创造性的,同时还具有一种传承性,但它又是“直接无力”的,一定要通过某种中介来对社会发挥作用。
而“观念的人”的基本关系或处境是来自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和处理两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第一,和行动精英、比如和经济领域内的企业家、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家的关系、但尤其重要的是处理与政治精英的关系;第二是和大众或民众的关系。前者古往今来一直突出地存在,它是一种精英内部的关系,是观念精英和行动精英的关系,是一个少数和另一个少数之间的关系;后者在现代社会才真正凸显,它是一种精英外部的关系,是精英和非精英的关系,是一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又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行动精英有可能利用大众来压制观念精英。
这样,现代的“观念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基本的困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有时会处在一种政治精英和大众夹迫的处境中。当然,两者所给的压力是不同的,前者往往通过硬性的权力、后者则主要通过比较软性的舆论和市场来起作用。还一种情况是一人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来压迫他们,这时“观念的人”大概就无处可逃了,但这种“极权主义”的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而“观念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其本性上说是要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的对象的,是要热爱观念和智慧的、是要与真理为友的。或至少可以说,他们是要关注他们所处理的观念是通过独立自由的思考而产生的,而不为其他利益或立场而扭曲的。独立就对他们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他们需要首先争取和始终保持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或还应澄清一个也许是源远流长的说法,即认为知识分子是被体力劳动者“供养”的。造成这一说法的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流行的一种崇拜简单直接的体力劳动,认为财富都是由体力劳动所创造的观点。于是,在大规模社会动员之后的激烈阶级斗争中,“被养”就曾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原罪,好像知识分子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就是吃白食的,他们得到的食物只是对他们特别的“恩赐”,如果不听话就得不到这份食物。据张颖在《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回忆说: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闭幕式的前一天,周恩来召集京剧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开会,作了鼓舞他们的讲话。但江青接着发言,严厉地责骂知识分子说:“解放这么些年,你们都在干什么?人民养活着你们,你们是在白白浪费人民给的粮食……”“这里她并不是将所有劳心者包括在”被养“之内,因为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对她自己,对所有政治的和管理的人员说的,甚至对所有掌握权力的人说的,而且,这样说是更有强得多的理由的,因为政治家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但江青或是认为她就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不用这样说自己。她甚至把服务人员对自己的态度视作是对”无产阶级“的态度,稍不顺心就斥责他们没有阶级感情。但这种对”人民“或”无产阶级“的垄断解释是可怕的。江青的讲话是”文革“即将发动的一个预兆,我们很快在”文革“中目睹了这一说法的悲惨后果。
然而,脑力劳动应当说也是一种劳动,脑力劳动也创造财富,甚至更大的财富。物质财富并不都是由体力劳动来创造的,”劳心者“的科技发明和推广、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不仅过去是、今天更加是物质财富的很重要来源,甚至可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另外,人还有其他的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如果仅仅是物质需要,那么人也就和其他动物完全一样了。而这种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是可以通过用物质的东西与文化的产品来自由交换的。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并不是由别人来养活的。那些通过呕心力作和自愿交换得到收入的知识分子是”自己在养活自己“,是”自食其力“而不是”受人供养“。我们赞美一切以体力劳动来养家糊口的人们,我们也应当同样赞美一切以智力劳动来养家糊口的人们。我们也许还要特别赞美如果不能以智力劳动养家--如果这有损他们的独立性--也能以体力和手工技艺养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磨镜片的斯宾诺莎。但无论如何,今天如果我们还继续持一种知识分子是”受人供养“的一种认识,那么,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就永远是有某种理由的,就总是有一把杀手锏可以对付他们,就可以通过摧毁他们的经济独立和道德人格来摧毁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自由。
【下一篇】【陈宜中】公民儒教的进路:陈明先生访谈录
作者文集更多
- 【何怀宏】君子的人格 12-29
- 【何怀宏 赵占居】将无同?岂无异?——··· 06-07
- 【何怀宏】我们想要怎样的人类文明? 08-11
- 【何怀宏】政治、人文与乡土 ——当代儒··· 07-06
- 【何怀宏】人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伦理道德··· 08-08
- 【何怀宏】对新文化运动人的观念的一个··· 10-28
- 【何怀宏】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 07-27
- 【何怀宏】抗议性政治不应成为主流 07-13
- 【新书】何怀宏:谈成功的书多,谈生··· 03-30
- 何怀宏著《新纲常》出版 11-19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