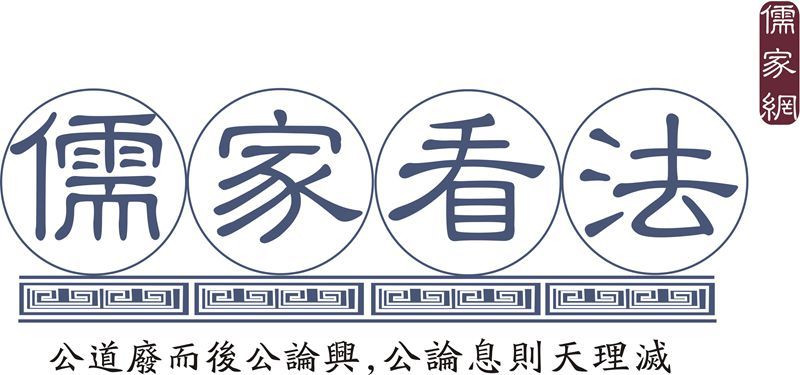【社评】母辱伤人,理应无罪;司法改革,势在必行

母辱伤人,理应无罪;司法改革,势在必行
社评
鲁人于欢,于2016年4月14日,因目睹其母遭受过分凌辱而伤人致死。近日,聊城地方法院判决其无期徒刑。此案甫一传出,几乎阅者哗然,批评判决不当而为于欢呼吁者,俨然已成为舆论主流。何以如此?值得深思。
依据报道,考察案情,原不复杂:于母苏某,向人借贷,因无力清偿,遭暴力催债,逆受11人之摧折侮辱一小时余。
死者杜某,更为渠魁,竟在于欢眼前,以极其下流之手段,对于母施以侮辱。于欢男儿,不堪其辱,愤而反抗,持水果刀,乱刺施暴之徒。四人受伤,其中杜某自驾就医,中途死亡。
照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理所当然。然而面对无期判决,举国之民情舆论,近乎哗然而不肯接受,为何?因为它悖逆了最起码之人伦常情。
古今中外,大凡善良法制,必以人情伦理为其重要基础;至于悖逆人伦而强恃法律,则自来为治国者之大忌。对此要点,深受儒家思想浸润之传统中华法系,不但有特别之注意,而且有高明之处置。
以复仇为例,实为人类文明之普遍现象。而吾国自秦汉以下,历朝律典之明文,大率皆禁止复仇,而于行法之时,尤其在司法运作中,又根据具体案情而予以相对缓和,甚至于有所鼓励。之所以禁止复仇,其理由在于家国天下之和平秩序必须维护;之所以鼓励复仇,其理由在于天生自然之人情伦理不可悖逆。
每有复仇类案件发生,必在国法与人情之间,发生各种较量,为防止社会撕裂,传统文化又有天理一目为之折冲。
三元之间,既离且济,构成传统中国法政世界“天理-国法-人情”之基本结构。凡遭遇人伦案件,历代名公皆在此三元结构中,予以权衡妥当,必求本于天理,顺于人情,合于国法,而完成良好之裁判,而所谓合于国法者,又往往以不违为准则。此间实蕴含有治国理民之大智慧,亦为传统民本法学之精义所在。至于极端情况,则传统名公之做法,宁可失于一时一处之国法,而不可悖逆普遍高悬之天理,与夫永久长存之人情,实乃更为可敬可佩。
论语有言:孝悌为仁之本。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着眼处,皆在于孝悌具有建构良好秩序之巨大能力。孔子作《春秋》而荣复仇,与此要点,似为逆行实则同归。
然而,晚近之百数十以来,天理涤荡,人情浇离,国法嚣张,思之令人悲从衷来。三元如此,而欲和合天下,治理国家,不亦难乎?念往年之夏俊峰案、范木根案、贾敬龙案等,若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三元结构中加以裁量,则断不致于逆乎人情而刻薄寡恩,而其判决亦必然可为大众所普遍接受,进而建立更高之司法公信力。
惜乎!三元结构之不存也!而今于欢一案,生母在眼前受辱,又无公权可援救济,方此之时,若不举刀而刺,于欢不独不可以再为人子,亦不可以继续为人也。此实为古今人情之至大,于此情境,当政不可不慎。
故而,就其眼前而言,于欢伤人,出于人情至善,理有必然,无可厚非。法律对于伤人害命,虽有一般禁令,然而对于此一特别案例,则不宜将其作归罪处置,即或归罪,亦必当轻刑。如今之判,自长远考虑,必定得不偿失。
况且,伤者死者之四人,或受伤或致死,皆有自己之重大过错在先,更不可主要归罪于欢。母辱伤人,虽终致死,理应无罪;民事纠纷,国法可依,另当别论。另一面,就其长远而言,借文化复兴之大势,吸收传统智慧而介入司法改革,可谓势在必行者也,若能在更高基础上,重建“天理-国法-人情”之良好司法结构,则更是造福当代,遗惠子孙,善莫大焉者也。
(时亮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