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培】关于西方《尚书》学研究新动向的思考 ——由《中国政治哲学之源:〈尚书〉 编纂及其思想研究》谈起
关于西方《尚书》学研究新动向的思考
——由《中国政治哲学之源:〈尚书〉 编纂及其思想研究》谈起
作者:赵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来源:“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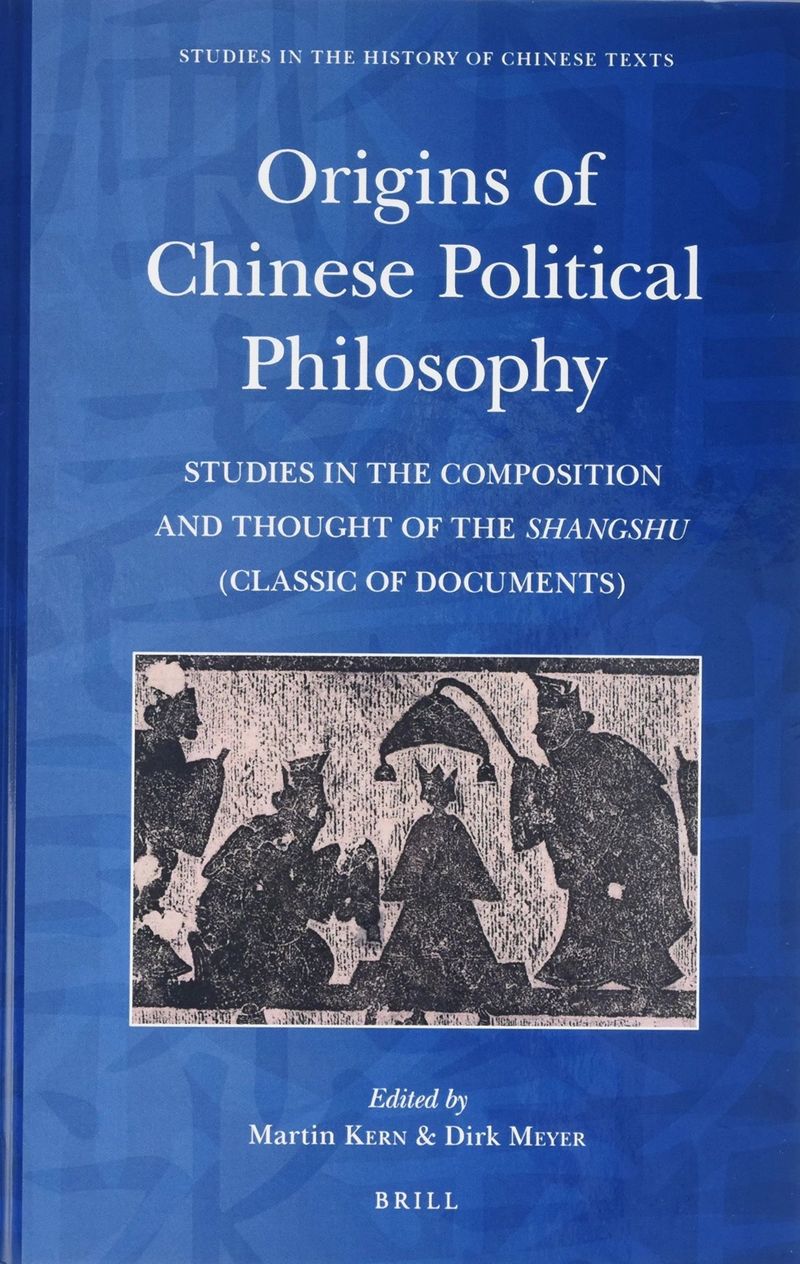
-410.jpg!article_800_auto)
2017年5月《中国政治哲学之源:〈尚书〉编纂及其思想研究》(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ought of the Shangshu (Classic of Documents))一书由博睿(BRILL)出版社推出。该论文集由柯马丁(Martin Kern)和麦笛(Dirk Meyer)主编,是西方汉学界《尚书》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收录了十四篇与《尚书》相关的研究文章,涉及到《尧典》《舜典》《禹贡》《金縢》《多士》《无逸》《多方》《顾命》《吕刑》《粊誓》等篇,论者结合传世与新见出土《书》类材料,通过多学科综合(multiple disciplinary)分析以及知识史的视角(intellectual perspectives),重新认识《尚书》及其所含篇章的文本性质和文本结构。在详细分析和阐释文本中的核心观点及箴戒思想的基础上,他们试图赋予《尚书》作为一个动态文化载体汇编的文本性质,认为《尚书》文本表达和塑造了不同时代、诸多学派的政治和知识话语体系。
此书是西方汉学界首部系统研究《尚书》的早期历史及其文本结构、语言特点和思想特征的著作。就其研究视角与所得结论而言,可以说它是对中西方《尚书》学研究传统的“双反动”。
西方《尚书》学肇端于1770年,法籍汉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在巴黎编辑出版了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翻译的《尚书》,当时用的是法文。1846年,《尚书》的首个英文译本由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译出,此书是随后(1865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书经》译本及1904年欧尔德(Walter Gorn Old,1864-1929)《书经》译本的先导。加上1897年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的法文译本,这些早期的译著构成了西方《尚书》学研究的基础。20世纪中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关于《尚书》的研究代表了当时乃至其后很长时间西方《尚书》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后,戴梅可(Micheal Nylan)、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艾兰(Sarah Allan)等学者均撰写过《尚书》相关的文章。从上述研究史来看,西方汉学界传统的《尚书》学研究,基本上接续着清代朴学或古史辨史学研究的传统,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异域视野”,直至这本论文集的出现。
一、《尚书》相关篇章的文本层次与思想层次
《中国政治哲学之源:〈尚书〉编纂及其思想研究》(下文简称《〈尚书〉编纂及其思想研究》)中很多文章都关注到《尚书》作为一个完整且又同质的文本,其内部的互异现象,并以此为突破口来讨论《尚书》篇章的文本层次与思想层次。沃格朗(Kai Vogelsang)的论题即为《〈尚书〉中互异的声音》,他以《尧典》《皋陶谟》和《吕刑》三篇为例,不仅分析了各篇内部语言特征及文本内容上的差异,也讨论了诸篇差异相合性,即三篇使用了近同的结构模型。三篇共享的这一模型暗示了各篇中的矛盾部分明显宣扬着不同的统治观,主要表现在对天命政治与理想官僚政府模型两种追求的共存。此三篇外,《尚书》其他篇章明显不具有合成特征,亦未表现出统一的语言和思想脉络。所以沃格朗认为,《尚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由整齐的文本与思想层次构成的。
同样,柯马丁(Martin Kern)的《〈尧典〉中的辞令与王权意识》一文亦认为此篇显然包括了尧和舜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虽然其并未给古文《尚书》翻案,但仍认为《尧典》(包括《舜典》)应该分为两部分来看。柯氏通过分析押韵、节律等修辞手段,认为关于尧的叙述部分应该是尧作为王的表演性演讲。关于舜的叙述部分,他认为无论是从用语还是从内容上看,其所表现出的天命思想,以及对统一政体的模拟等,根本上不同于尧叙述中所呈现出的古老王权模型。此外,文章还认为,较之尧的个人魅力及非凡特质,舜似乎仅仅作为官僚机制背后的某种力量存在,故而认定关于舜的叙述应该是一个更晚的文本层次。
与之相类,陈力强(Charles Sanft)的《〈尚书〉中的法律概念》,讨论了《尚书》诸篇内容所反映出当时对法律和法律活动的认识。文章认为《吕刑》所提出的法律实践及法律观念同《尚书》其他相关篇章形成巨大差异,多数篇章(包括常见征引的《康诰》)均认为刑法手段是必须的,但最理想的社会还是应该弃刑;而《吕刑》认为适当的刑法本质上是有益的。实际上是从法律视角彰显了《尚书》在文本和思想整体上的层次性。
以上三篇文章,展示了文本与其所反映思想层次性的两类情况:一是单篇内部的层次性;二是《尚书》作为整体其诸篇之间所显示出来的层次性。我们发现,三篇文章更关注也着力在证明此种层次性的存在,至于其出现的动力因素则并未深及。
二、《尚书》相关篇章的编纂时间重估
麦笛(Dirk Meyer)在《“书”的传统与文本重纂:〈金縢〉和〈周武王有疾〉篇价值重估》一文中清楚点明,其研究参考了米克·巴尔(Mike Bal)的叙事学和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记忆生产理论。麦笛关注文本化的“书”生产和流传过程中,知识本身的流播问题。故而他将“书”的传统放在动态的文化视野中来分析,考察其众多成分的不断变化情况,以及在不同的背景和条件下,如何不断地被新的团体以新的形势再界定。就简本与传世本《金縢》而言,他认为前者是经过细心编写,以昭示对周公廉洁无私品格的怀疑,但最终目的是为了祛除这种不信任。所以简本不同于传世本,从修辞目的上,诸多叙事元素表现出严格的层次结构,显示出丰富的戏剧性。简言之,简本不同于传世本,其曾作为表演性文本被使用过。
麦笛另有一篇《文本的语境重构与记忆生产:从〈顾命〉篇重建关于统治地位的论辩》,详细分析了《顾命》的文本,将其与清华简《保训》进行对比分析。麦笛认为这类文本共享了同样的文本模型,而这种稳定的模型形成于战国时期。战国时候的很多事件都通过这一模型呈现。通过这种文本生产的修辞范式,一个历史事件被再现为前后连贯的文本,这一事件就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种事件类型。将这些叙事类型放在整个叙事传统中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一类型不仅为已发生的事件设置了框架,并且拓展了历史叙述的新的维度。正是在这样的叙事维度上,不同学派借助过去来树立自身的权威与文化身份。麦笛认为,诸如《顾命》和《保训》一类的文本,只可能在战国时期编纂出来,但其中可能包含有作为当时社会政治和哲学辩论的工具而存在的更早的文本层次。
同样,柯马丁《〈尚书〉中的“誓”》首先分析了《尚书》中“誓”类篇目共同的修辞、语言特征、文本类型和意图,这一特点具有历时性,显示出此类文本结构性与仪式化的特质。柯马丁认为这些“誓”类篇章应该是对周文化记忆的追溯性创作。这些篇章总是将讲演者描绘成为勇武且道德完美者,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它们总是为古代中国的战争披上天命的合法外衣。从语言上来看,柯马丁认为这类演说曾被用作实际演出文本,至少其中的部分篇章曾被放到礼仪场合表演过。
史嘉柏(David Schaberg)《文献之声:战国文本中的引〈书〉材料研究》一文认为,《尚书》表面上是一个“书”类文献的合集,实际上其中包含着以书面形式书写的早期演说。在仪式拟古主义的修辞模型标记下,这种书面形式将早期权威的王室话语形式保留在了被记录下的演说中。一直到数个世纪之后的春秋,甚至早期帝国时期,这种形式一直传承,如秦刻石与汉祭祀歌等。史嘉柏认为,如果《尚书》是以书面的形式存档保存,那么这些早期书写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口传文化当中,《尚书》中的很多篇章实际上是对动态口传文化的静态录存。史嘉柏通过对战国文本中的“书”类引文的详细分析,认为当时同样的仪式拟古主义者对保存古代材料以及新的仿古文体做出了贡献,较之阅读《书》篇,他们更在意文本中的口头记忆。
夏玉婷(Maria Khayutina)《〈粊誓〉,西周盟誓文本与早期中国的法律文化》一文探讨西周“誓”类文本和法律文化问题,文章集中讨论《粊誓》篇。夏玉婷对传统上将此篇作者归属于伯禽的说法提出质疑。通过比较西周铜器铭文,她认为《粊誓》不可能早到伯禽时候,尽管此篇文献反映了西周法律文化,记录了当时的活动,语言上具有相似性。结合其他纪念性文本,如《左传》和其他早期文献中的各种历史参考,夏氏认为,《粊誓》在鲁国产生出来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段,或者更晚。因此,她认为此篇是地方政府记忆文化的产物,是通过模仿周王室的“誓”篇的纪念性文本,服务于政治权力的象征性表现,通常是为了转移当时的危机。
三、《尚书》《逸周书》的类分
葛觉智(Yegor Grebnev)在《作为记言文本实例的〈尚书〉与〈逸周书〉》一文中,以形式评析法(Form Criticism)为基础,系统吸收了西方学者文本分析的既有方法,试图确立新的标准对《尚书》《逸周书》及更多相关文献的文本进行更为“科学”“准确”的分类。其方法中关于语言、修辞等标准的使用,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中已多有尝试,汉语史领域的研究中更是属于基本方法;其所用的语境分析法(Contextualization),在此论文集中已非特例。所以,葛氏的研究并非新在独创,而是新在综而用之。此文通过对相关篇目文本类型、文本修辞、文本结构,以及语言细节的描述和对比、词汇分布等方面的分析,根据文本材料的性质,将其分为叙述(Narrative)和记言(Speech)两类。实则与《汉书·艺文志》所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相类。为了合理解释记言类文本中的叙述成分,他将叙述文本限定在纯粹叙述文本(Speech-independent Narrative),而认为记言文本中的叙述内容实际上服务于记言需要,因此依然判定其为记言类。
据其类分,葛氏认为除《禹贡》外,今本《尚书》中今文类均属于记言类文本,而《逸周书》中记言类则包括《大匡》《程典》《酆保》《大开》《小开》《文儆》《文传》《柔武》《大开武》《小开武》《宝典》《酆谋》《寤儆》《和寤》《大匡》《文政》《大聚》《商誓》《度邑》《武儆》《五权》《成开》《皇门》《大戒》《尝麦》《本典》《官人》《王会》《祭公》《芮良夫》《太子晋》《殷祝》《周祝》,共33篇。
另外,在赫尔姆特·乌茨施耐德(Helmut Utzschneider)和柯马丁相关论说的基础上,葛氏又将《书》类篇章进行了戏剧化(Dramatic)与非戏剧化(Nondramatic)的区分。在进行戏剧化与非戏剧化区分的时候,葛氏运用了一些语言学的知识,如根据一二人称代词、感叹词等的分布来进行判断。他认为在记言类文本中,具有非戏剧化特征者,上述词汇要素多出现在开篇和收尾处,而具有戏剧化特征的文本,则上述要素分布比较均匀。
此外,葛氏还参用了语境分析法(Contextualization)和目录分析法(Catalogs)。其中目录分析法是基于这样一个认定,那就是战国时期的文本在安排和处理知识时有时会有系列化的清单,近同于制定目录,葛氏用以强调文本中存在大量序列化的知识,也即有些文本在内容安排上具有序列化的特征。
综合使用以上方法,葛氏将文本类型划为五种。第一种类型是戏剧化的记言文本,包括《尚书》中的《甘誓》《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之命》《牧誓》《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诸篇;《逸周书》中的《商誓》《度邑》《祭公》诸篇。第二类是非戏剧化的记言文本,包括《尚书》中的《洪范》,《逸周书》中的《酆保》《大开》《小开》《文传》《柔武》《大开武》《小开武》《宝典》《酆谋》《大匡》《文政》《大聚》《五权》《成开》《大戒》《本典》诸篇。第三类是述梦文本(Dream Revelation),包括《逸周书》中的《文儆》《寤儆》《武儆》。第四种类型是书面通告类文本(Writing-informed),包括《尚书》中的《吕刑》,《逸周书》中的《大匡》《程典》《芮良夫》。第五类是基于情节的对话体叙述类文本(Plot-Based Stories with Dialogues),包括《尚书》中的《金縢》,《逸周书》中的《太子晋》《殷祝》两篇。
以上五种类型实际上难以囊括所有《书》篇,所以葛氏又将剩余的分作第六类,包括《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高宗肜日》《梓材》《顾命》,《逸周书》中的《和寤》《皇门》《尝麦》《官人》《王会》《周祝》诸篇。从例外的这十一篇来看,试图确立新的类型标准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而葛氏的努力自然也是其尝试行为本身的意义大于所得结论。
四、传世与简本《金縢》当分读说
随着出土文献越来越多,有传世文献可对读的篇目数量也在增多。目前对于此类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从新字释读到缀简、断句等,多参考传世篇章来进行。然而,若出土篇章和传世篇章,仅仅是表象上的互文,实则属于不同性质的文本,那么以上对读分析研究的方法就难免出现偏差,甚或失误。Magnus Ribbing Gren的《清华简〈金縢〉篇:我们所不知道的周公》一文试图来讨论此问题。文章详细分析了清华简《金縢》及其平行文本《尚书·金縢》篇,从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揭示出土文本同传世本的差异,最终认为两者应该独立阅读。Gren认为,在传世本《尚书》中,周公以己为牺牲来代替病重的武王,简本中周公则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继位的野心,因此简本其实是武王退位给其贤能兄弟这一叙事模型的延续(相近叙事见载于《逸周书》)。Gren还认为,战国时候,学者热衷于讨论王位继承原则的问题,同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然而这些讨论在秦汉帝国时期逐渐消失。所以Gren倾向于认为在战国和秦汉帝国时期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金縢》故事,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意涵。
若抛开这篇文章讨论的具体对象和具体结论的争论,我们认为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提醒,传世与出土文献对读的时候,切记不要直接用既存的知识体系去框套新出土的文本,而应该为传统知识体系预留下被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五、《尚书》学研究的新启示
以上简单介绍了《〈尚书〉编纂及其思想研究》一书的主要篇章,着重分析了它们所用材料、方法及得出的结论。总体而言,多数学者受到文化记忆理论的影响,擅长通过语言特征、文体结构模型,尤其是文本的哲学意涵分析,来讨论《尚书》及其篇章编纂的时代性与目的性。他们强调文本生成背景的特殊性,例如王朝衰颓时或灭亡之后,子孙对先王先公的追怀促成了文本生产行为等。另外,他们还强调文本的表演性特征,注意从仪式功能角度去讨论文本,反之同样关注文本中的表演性特征。在文化记忆理论基础上来处理《尚书》文本,确实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鲜感,然而《尚书》也实实在在地被理论框架及其所对应的前期预设所切割,更像是证明某一理论的素材而非研究对象本身。
回顾《尚书》学研究史,重视文本的内在矛盾性、语言特征以及哲学意涵(思想特征)的分析法,同古史辨派的研究近同。我们知道,古史辨派及相关人员的辨伪事业,颇受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今文经派的影响,其辨伪书,以做成“伪史”为目的,论断甚为悍勇。当时的学者,如张荫麟、胡适和叶青三位先生,已开始反思当时古籍考订方法及其逻辑依据上的问题。① 那时所提出的问题,如默证陷阱、语言和思想判定上的主观性等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值得重视,因为前述诸篇在论证逻辑上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此外,“文化记忆”派多数论者将篇章的形成时间锁定在战国,或者更晚的时候,同古史辨派学者的结论亦近同。然而,古史辨派的研究确实将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并不受限于某一理论框架,又可见出二者近而不同。
另外,此书是西方汉学界停滞既久的《尚书》学研究新起点,必然存在着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文本分析的前提是对文本内容的强有力的掌控力,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丰富而全面的相关背景知识,若有缺环,则极易误读误判。如尤锐(Yuri Pines)在《一位勤劳之君?重读〈无逸〉》篇中,论说此篇讲到统治者在就任之前作为体力劳动者的经历,认为其很可能并非直接继承王位,而《无逸》实际上表达了此王对传统权力交接原则的质疑。由此他认为,这一独特的视角,虽未被其后的传注家们所注意,或许反映了此篇编撰的特殊背景,极有可能是前771年西周王朝瓦解后的结果。这里的论证基础仅仅是《无逸》开篇部分所见的周公曰“先知稼穑之艰难”,然后生发出上面的双重推测。实际上,周人重稼穑,从后稷开始已然。蔡沈《书集传》言:“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鱼无水则死,木无水土则枯,民非稼穑则无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为帝,禹稷躬耕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劳于稼穑,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穑,周公发《无逸》之训而首及乎此,有以哉!”②所论较尤氏的说法更为妥当。再者,文本层次背后对应的不仅仅是文本形成问题,亦可能是文本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改变,若结合中国起源甚早的史官传统,则后一种原因的可能性似乎更大。“文化记忆”派学者将文本和思想层次出现的原因直接归因到文本生产上去,颇显武断。
尽管这些初始研究尚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对自己所提出问题的论证和解释力度上存在不足,但是他们所指出的这些现象在《尚书》文本中确实存在。如《尚书》作为一个动态文化载体汇编,其单篇内文本层次,多篇之间的思想差异,《尚书》及其篇章生产的目的,相关篇章的表演性特征等问题,确实值得做更深入研究。推而言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古书及其篇章形成和流传背后深层次的动力因素。古书形态的变化(包括载体形态和文本形态)、流传渠道和方式的转变,以及经典的诞生,不是简牍篇章的简单拼合,而是跟时局之转、文化之变以及新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群体的出现等因素直接相关。分析《尚书》文本演变的诸多现象,探析这些现象所关涉到的传统变革、文化转向、政治形态、学派意图等更深层的问题,将是《尚书》学研究的新方向。
注释:
①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衡》1925年第40期,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2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9页;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哲学论丛》(第1集)1933年,收入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6册),第263-276页;叶青:《从方法论上评〈老子〉考》,《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第1卷第6期,收入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6册),第283-296页。
②蔡沈:《书集传》,日本汉文大系孔传、蔡传合刻本《尚书》卷第九,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78年影印,第16页。
责任编辑:近复
【上一篇】王杰著《家风十五讲》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下一篇】【张传海】“家人嗃嗃,悔厉,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