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锋】传统经学在当代传受的三个层面
传统经学在当代传受的三个层面
作者:罗云锋(华东政法大学)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载《儒家广论:松江先生卮言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p186-196。稍有改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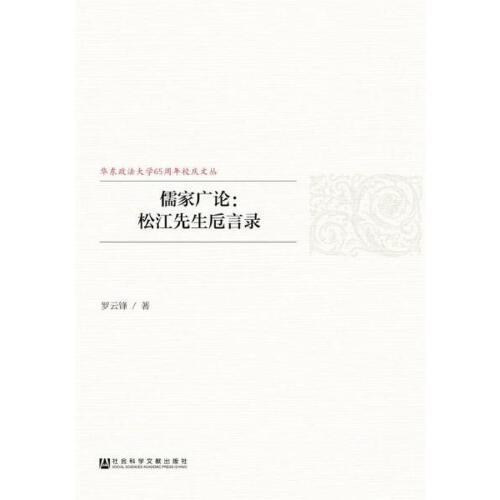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日益强调传统文化复兴和中国文化主体性,由此促成了对于传统思想文化典籍的出版、阅读和研究的热潮。大体而言,传统中华文化乃是儒释道三位一体,此外又有诸子百家等为之辅翼。儒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诸子百家之思想,而成为中华文化之主流,经学则为儒家思想之渊薮,而“十三经”又为经学之核心。故谈及传统文化复兴和创造性转化,便涉及传统经学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接受问题,本文将对此论题作一讨论。因笔者另有文章谈及“对照经学”和“新经学”,故在本文亦以旧经学来称呼传统经学。
一、旧经学传受的三个层面
关于旧经学(乃至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传受的状况,当然亦涉及典籍版本的问题,更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却是:当代中国是以什么方式、从什么层次水平来传受旧经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就前者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旧经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极为活跃,整理出版了包括儒家“十三经”在内的大量传统文化典籍,形式多样,版本丰富,读者选择面大,为旧经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创造性转化及其优秀成分的传承、普及和复兴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基础性的工作。但如果从接受的方式、层次这一角度来分析,则亦存在着某些问题,比如,一方面,许多新整理的版本对旧经学往往停留在文字训诂或文学欣赏的层面,往往并未深入到经义层面;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关于旧经学的学术研究著作又多为专家之学,多繁琐之名物训诂与考据等,虽亦杂有经义方面的阐述,而在文风上往往盘庚诰古、佶屈聱牙,一般读者难以卒读。而重在经义存真而兼顾经义训诂且便于阅读的好的本子其实并不多。
以旧经学为例,以笔者的观察分析,当下对旧经学的接受或传受,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1)文辞之学(文学书,对应于辞章):偏重文学辞章层面,亦稍涉音韵训诂。此为旧经学或传统文化传受的最浅显层次,亦为旧经学或传统文化入门之始基,即通过字词之音韵训诂、文句之诵读记忆以及词章之抑扬唱叹之领悟,获得阅读、研究旧经学的基本文史知识。然而,虽曰经学入门之始基,却并不系统深入,尤其是不得旧经学之精髓核心(经义典章等),只是停留在字词解释和辞章层面,故由此所得者少而浅。其中亦有一部分间涉经义,然而往往浅尝辄止乃至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其稍好者或能发挥宋学精神,而作经义之发挥,其次者则胡乱发挥,乃至处理成心灵鸡汤,失却了经义层面之严肃探讨和领悟教益。经过三十年来之学术发展,此一层次之古籍版本甚多,比如各种译注、文白对照、简易注释乃至白话经典等本子等,其中亦有较高质量者,读者自可择其善者读之,以引发阅读者之兴趣。
(2)经义之学(经书,或大致相当于义理):关注经学义理层面。此为经学本来面目,今世之所谓经学研究,乃至所谓读经或经学传受,其实就应落实在这一层面,而不是寻章摘句、记诵文辞的层面。质言之,无论是批判(其缺陷者)还是继承(其优秀者),今日谈阅读、传受和研究传统文化或旧经学,便须首先注意其中之经义本身。要达成此一目的,首先便须重视整理制定旧经学或“经义之学”的相对完善、优良之版本,以此作为广大学士、国民、研究者阅读、研究、批判继承与普及经义之学(中之优秀者)的“善本”(非版本目录学意义上的“善本”也)或通行本。与此目的相适应,则好的旧经学本子应当符合如下标准:深切、详明、雅畅,亦即深入-经义、切实-存真、详瞻-丰厚、明晰(兼简明)-逻辑、文雅(或文言)-美感(熏陶)、畅达-易读,以为旧经学的传受贡献出较为经典的通行版本。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当下的传统文化出版物,则仍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尤其是在旧经学典籍层面,好的版本仍然相对较少,有些只能满足其中一两条或多条,而不能全数满足以成旧经学之良好版本或通行本。
(3)专家之学(专书,或大致相当于所谓的考据之学或考论分析研究之论著):偏重学术研究层面。虽然当下并无通儒或经学大家,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几十年来,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亦培养了一大批文史专家学者,同时,传统文化的整理、普及、研究工作亦有很大的发展,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经学的研究整理方面,亦有特别之表现和成绩,出现了一大批相关专书,比如中华书局推出的“十三经清人注疏”之整理本以及其他学术研究著述等。这种著述属于专家之学,极有价值,亦极为必要,而成为经学不断发展之源头活水,学术价值非常高。然而这类著述版本重在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严肃之学术研究和学术发现(或有汉学、朴学之遗风),不重在经义之阐述普及,亦不易读,即难为普通学士国民所阅读,故难以承担起作为传统经学通行本的任务。
以上为旧经学中所蕴含的三个关注层次。当然,就旧经学本身而言,则包括更多方面和层面的内容,举凡道学、哲学、伦理、典章制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礼仪、名物、文学乃至科技等,无不蕴含包纳之,而为通人之学。本文为了分析的方便,在经学内部将其分为文辞之学与经义之学两个层面,所谓文辞之学,乃指其外在语言形式方面,而经义之学则强调其内在精神、思想层面,而举凡上述除了文学之外的种种内容皆可包含其中,而经义(义理)、典章制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礼制等诸方面之典章制度)尤其是典章制度之法度立意(立法原则、立法精神)、礼制及其命意等实为其核心,至于具体名物等方面,由于时代之变迁,倒并非关键,虽然对于理解经义亦不可或缺。但其根本则在经义,以经义总以上诸学。此虽不类于西方分科之学之逻辑体系,然此恰为中国经学之特色和特别价值所在,而可于少数若干本经典著作中得到丰富全面之熏陶教益。质言之,本文之所以特别拈出文辞之学、经义之学和专家之学,乃是基于问题意识而立论,并非否认经学本身亦包括辞章之学等广泛内容领域。
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是:文辞之学是经学或经义之学的基础,即为学士读者的经义之学打基础;专家之学是经学或经义之学的指导与发展,即为经义之学提供高水平学术支持;而经义之学则是经学的内核,是文辞之学与专家之学的最后归依。经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经义之学或道义之学。倘徒以文辞之书视之,则所得唯文学辞章及零碎肤浅之义理、名物等知识而已,只是文学或记诵之学,失却经学之本意与大体。质言之,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经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而必须入于经义之学的层面方可,此为传统文化之基本内核所在,不然空得浮文辞章,乃至思维笼统混乱、思想肤浅割裂之弊病,而不见“士志于道”(古之仁道、中道、天道与近世以来之救国救民、强国富民、人民主权等之新道)之志气风神、仁德节义之修养品格、政教典章之循道法筹措处事能力,如此则似无须阅读古典而径读今学可也。
二、旧经学通行本的两种思路:经学旧疏与经学新疏
严格地说,上述旧经学的其他两个层次也非常重要,但针对旧经学在当代传受的现状,作为问题意识,则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言,尤其要重视经义之学层面的研究、显明、批判、扬弃而后传受。质言之,对旧经学的传受,无论是旨在了解、濡染而取其精华,还是批判分析,都应当特别注重经义本身。然而,现实上的情形却是,许多传统典籍和旧经学版本要么往往将之处理成文学辞章之学(比如不少版本将《诗经》处理成文学文本),要么则是繁琐考证而略显晦涩的专家之学,所以在经义之学这一层面,真正原汁原味的传统典籍尤其是旧经学的注疏版本并不多,即较为缺乏经学大家或学问大家来从事经义之学那一层面的阐述,整理出较好的旧经学通行本子,而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
故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经义之学的通行普及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传统经义之学及其通行本的整理撰述。关于这点,可以有两个思路或进路:第一,整理旧经典旧注疏版本;第二,整理旧经典之新注疏版本。
先论第一种路径。
由于既有文教学术水平等的限制,在一时无法结合古今大道而融通创作新经学、甚至一时无法整理撰述出更好的旧经学之注疏版本的情形下——在整体文教学术水平、学术人才、才学水平等尚不能提供相关支撑或支持的状况下,亦不宜急于创制——,当下便可退而求其次,先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第一点,整理出更好的旧经学注疏通行本等。毋庸置疑,到目前为止,南宋绍熙年间所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合刊《十三经注疏》(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则是迄今为止最为精善的版本),是唐宋以来最好的经学通行本。从古典经学传授、普及或文“化”(有文而化,道文化及)的角度来看,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超过它的更好的本子,而为其中之翘楚。清代学者虽然在经学研究上做出了极大的成绩,其经学研究著作亦有极高学术价值,然终究多为专家之学,偏重于研究和考据,在经义疏通畅达和便于通行而作为通行版本方面,未必是其撰述重心,故仍然有其局限,未必能膺此重任。故先不妨整理《十三经注疏》的通行本子,等将来时机成熟,再尝试旧经学之新注疏版本的整理撰述,并将清人的研究成果纳入进来。
所以,以下笔者便以《十三经注疏》的整理出版为例具体论述之。显然,《十三经注疏》承载了传统经学、儒家文化乃至传统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内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当下的整理出版情形稍作打量,便发现情形仍然不尽如人意。目前,当代关于全本《十三经注疏》的整理出版,较好的版本,计有中华书局五卷本的影印版《十三经注疏》(2009年10月版,字体稍大,便于阅读)、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缩印本(两卷本,1997年7月版)(以上两个版本皆影印自世界书局重排本,无句读)、浙江古籍出版社之缩印本(两卷本,1998年6月版)、东方出版社的《明版闽刻十三经注疏》(全八册,底本乃是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之藏本,2011年7月版),以及台湾艺文书局八卷本的影印版《十三经注疏》(底本乃是嘉庆二十年江西府学刻本,较为清晰,八卷本亦便于翻阅,颇得读者青睐)等几种。这些版本大都是影印版,底本亦较为权威(闽刻本除外),是比较精良的本子。然而因为缺乏句读、缩印开本小、字体或有不清晰、分册过少而颇为厚重、翻阅携带不易以及校勘仍存不足(比如未能吸收清代的许多经学研究成果等)等因素,而不利于阅读,不能作为旧经学注疏之通行本。
而在单行本方面,则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十三经注疏》的重排单行本(全21册,1999年12月版,据称“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参见本丛书“整理说明”)),简体横排,版式较便于阅读,亦有繁体竖排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三经注疏》单行重排本(目前已出《尚书正义》、《周礼注疏》、《毛诗注疏》、《仪礼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等七种),开本较大,版式合理,经文与注疏在段落、字体和墨色等方面皆有明确之区分,字体清晰,十分便于阅读,是笔者最为欣赏的重排本版式。这两种《十三经注疏》的单行重排本试图对经典旧经学版本进行重新校勘,打造新时代的经典通行版本,体现了某种文化责任感、担当意识等良好之心志意图,获得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相当肯定,这从读者对两者的追捧购买便可见一斑(北大版因出版较早而早已售罄,而上古版每出一本,笔者即购买之),由此亦可见,学术界和社会上对好的旧经学通行本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高的。
然而,虽曰当代所出的较好的版本,上述两者却仍有其某些不足之处。但毕竟是目前为止较好的本子,故在更好的本子出来之前,便不妨将此两者尤其是上古版作为旧经学旧注疏的通行本子。
此外则有各种参差不齐的注释本、译注本、普及本和研究专书,其出版宗旨、关切点和针对的读者对象都不一样,质量亦良莠不齐,又往往偏于辞章与学术研究,故不甚适宜成为旧经学的通行本子。不过,在这些注释本子之中,笔者亦颇为欣赏刘尚慈的《春秋公羊传译注》的著述体式,此书在学术本身甚为扎实,而既稍有字词分析,又注重史事之分疏,尤其注意经义之阐发,由此注重了经学或经义之学的本质;译注语言亦文亦白,又穿插保留若干原始印证文字,十分便于阅读理解和保留古代经典之面貌;在版式上则采取繁体横排,便于阅读。这样一种著述体式,或亦可作为旧经学旧注疏通行本、旧经学新注疏通行本乃至批判经学通行本之著述形式的良好资鉴。
总体而言,关于旧经学通行本,如果根据上述六点要求来衡量,则较为缺乏符合标准的精善本子,故在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时代形势下,亦对整理出精善的旧经学通行本,提出了十分迫切而又高标准的要求。不过,在上述整理本中,笔者却十分喜欢亦十分看好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重排本(亦十分赞同其版式;北大版的版式亦可借鉴,惜乎是简体),故对上古版寄予了更大的期望。
次论第二种路径。
当通过文教出版事业等的齐头并进,传统文化和经学在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获得良好之普及和浓厚之学术氛围,培养出了大量经过良好训练的经学的专才乃至通才,则在条件成熟的形势下,便可尝试致力于旧经学之新注疏的整理撰述,换言之,整理撰述出超越古人《十三经注疏》的旧经学注疏本,以为有意之学子和读者提供更好的经学注疏通行本(经义深切畅达,版式适宜方便)——当然,在这一阶段,仍然遵循深切存真之原则,而谨守分际于旧经学的思想格局和学术范型内。以下将分别从整理旧经典之新注疏版本的宗旨原则、入手方法、标准、对撰述者的要求、版式体式创新等几个层面进一步申论之。
第一,就其宗旨原则而论,旧经典之新注疏版本之整理撰述,仍应严格遵循“首重经义”和“存真”(存经学之本真面目)之原则,既要将清代学者和现代学者之经学研究成果纳入新注疏版本中,又要尽量展示旧经学的学术本真面目,维持旧经学的立言宗旨、根本精神和经学体式——此亦是经学的优点、特点及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本身。尤其是要重点落实在经义之学的层面,关于这点,此处且以《诗经》为例稍作阐述。
比之于《春秋》、《尚书》、《周礼》等经书之往往相对偏重于谈论贵族或统治阶层之事,《诗经》倒是表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涉及更为广泛的阶层和群体,就此而言,《诗经》或可作国民读物。但有人认为《诗经》作为国民读物其实只有语言文学的价值而已,所谓《诗经》的诗教价值不过是经书传承过程中后儒附会添加的意义而已,颇为牵强,且多不合现代精神和现代价值者,故不必讲。本着这一偏颇之理解,有些译注版本便将《诗经》处理成纯文学作品即上述所谓文辞之学,对其诗教精神不过偶以三言两语蜻蜓点水提几句,或者根本不谈。然而,如果仅取其语言文学价值,则《诗经》未必能在经学体系结构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精粹的唯一或首要代表,某种意义上,许多作品、选本乃至古代文学作品选反而倒是比其更为合适。其实,《诗经》之所以成为儒家经典或经学典籍之一,显然不在于其文学价值,而尤其在于诗教精神:“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刺过讥失之二事耳。”(《毛诗注疏·诗谱序》之注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名。”(《毛诗注疏·诗谱序》)“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陈诸国之诗者,将以知其缺失,省方设教,为黜陟。”(《周南召南谱》)。“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注疏》)。质言之,《诗经》讲究风教美刺,其中,正风正雅(“风雅之正经”)是论功颂德,变风变雅是刺过讥失,而《诗经》之“美刺”与《春秋》之褒贬讥刺,其命意一也。倘无此诗教精神,《诗经》便退为一种文学经典——正如经学失其独尊地位、退而成为诸多经典或古典之一类一样(这当然有其古今转换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成为与《楚辞》、唐诗宋词等众多中国文学经典并列的品类之一,而当退出经学体系了(某种意义上,《唐诗三百首》、《楚辞》、《乐府诗集》、《文选》、《古文观止》等,单就其文学价值而言,未必就比《诗经》低)。所以,对于旧经典之新注疏版本之整理撰述而言,仍须本着存真的宗旨与原则,将《诗经》之诗教精神揭橥出来,而后对其内容分别或批判或扬弃继承,自无不可也。
第二,在入手方法上,可采取两种方式:单人注疏单经;或一人编注群经。也就是说,既可由学有专长或专治一经的学者采取单经注疏的方式来整理撰述,亦可由通经之通儒硕学对《十三经》进行通盘注疏之,即所谓的“遍注群经”的方式,比如郑玄、朱子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编注群经”的旧经典注疏整理之集大成者。此外,亦可借鉴古代“敕修”之遗意而”采取国家介入的方式,比如,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挂名督修,既可起支持督责之作用,亦可收倡导社会文化事业和风气、提倡传统文化之功效,上行下效,而促成此一时代之文化盛事,成为真正经得起学术考验的新时代经典版本,或新时代之传统经学之通行本。当然,如果采取这种方式,则当须选择此种领域之最好学者,既有外在督责,尤当内自矢志而倾力为之,而不是占着名号机会,敷衍塞责了事。此外,还可以采取鼓励学者自由著述的方式来进行,由中国有心志愿力的最优秀之学者自告奋勇、各自膺任撰述之,而后经由时间的检验,大浪淘沙,逐渐形成新时代的经学通行本——这亦是一种重要之进路。
第三,关于旧经学新注疏之标准,仍为上文所揭橥的六条:即深而切、详而明、雅而畅。其实,当代亦有许多旧经学和传统文化典籍的现代整理版本,有些亦十分扎实,甚至主要落实在经义之学上,而不是一般地处理成文辞之学或文史之学,但在达成上述六个标准方面,仍有一定差距,故难以成为新时代旧经学的通行的注疏本子,这也间接对优良的本子的整理提出了急迫的要求(笔者个人认为前述刘尚慈之《春秋公羊传译注》之版本体式皆甚好,或可作资鉴)。值得注意的是,在注疏文体上,最好仍用文言文方式来进行注疏,质言之,以文辞之学传经义之学,方不失传统经学之神韵神髓。
另外,在撰述旧经学之新注疏本子以作为经学之通行本方面,应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学术标准。其实,所谓的旧经学新注疏之“通行本”云云,其实标准和要求都不低,只是相对于专书之繁琐考证、佶屈聱牙、晦涩不文等特点而言罢了。质言之,旧经学新注疏之通行本之撰述原则和选择标准(从其从众多注疏版本中大浪淘沙、披沙拣金而言)应是:宁可从其高从其精深,不可就其低就其浅显,因为经学本来就含有向上提升之意,旨在向上提升人之精神品格、气度格局和眼光见识等,如果从一开始便立意就其低浅,则便难以提升之,亦即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此点不可不察!现在有些传统文化出版物虽然意在普及,亦有其一定之功用,然而倘若从经学的高度来衡量,则不可以此定通行本,即不可为通行与普及而降格,为低层次的通行与普及而而降低经学品格和学术水准。
第四,旧经学之新注疏整理,对撰述者在学问才力等方面的要求也更高。在撰著者之资格条件方面,心志、学问、才力(包括文才),三者缺一不可。心志则所谓“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真正之中国精神(“士志于道”之士人心志精神等)。学问则可有专治一经、通贯群经、遍览经史、通贯国学中学等几个层次,在经义、典章制度、史地、礼制、名物以及音韵训诂、辞章文学等方面,都要有精深的学养造诣。质言之,学问可分别从旧式通人之学(通儒或通经之学)、专家之学(经师或经学博士)、辞章之学乃至见识格局、学术能力等几个层面来理解。才力包括才与力,才则文才也,须有辞章之学,方能以典雅准确而有条理之文言撰述,而不改经学注疏之基本体式;力则愿力、意志力也,无其大愿力、大意志力,自然难以矢志不移而终生精研谭思、倾力为之。质言之,对于旧经学之新注疏之撰述事业而言,必有绝大之心志、学问与才力而后可,非其人则难膺此任也。倘无其学术,即使勉强膺之,亦可能画虎类犬,亦不克造就真正之经典版本。不过,毋庸讳言的事实是,在现今之时代,确实缺乏经学通儒或经学大师,故这样的任务,亦是任重道远。
第五,版式体式创新。在版式体例上,亦当有创新,而为新时代传统文化之通行和普及做出新的贡献。比如,依笔者的意见,繁体竖排,繁体横排等皆甚好;经原文与注疏文字,在字体、字号、墨色、段落等方面,皆当有所区分,字号亦应加大,排版应更疏朗一些,墨色亦当深一点,以便于阅读;校勘之位置安排亦当斟酌之,等等。当代的许多传统典籍版本,为了节省纸张等经济层面之考虑,排版上往往密实挤压,对于经、注疏或注释等,虽然在字号上有所区分,却不能在墨色上有所区分;字体稍小,排版亦较密,颇有压迫感,故阅读起来颇不方便,甚伤目力,有时竟导致读者意兴阑珊,不欲再读,此皆出版方面之责也。反而如果去看古代的线装书,开本更大,字体更大,排版更为疏朗,清晰宛然,经与注疏等皆有清晰区分,故读来赏心悦目,又不大伤目力,所以往往能手不释卷、怡然品读终卷。
不过,许多出版社亦在进行改进,比如中华书局的《谷梁古义疏》便于此有所尝试创新,而在经原本与注疏文字之间,在字号、墨色上皆有显著区分,但在经原文和注疏文字之间,仍未分别独立分段,经原文每被打断,读之乃有上气不接下气之感。而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十三经注疏》之重排单行本的版式处理便更好一些,可作为包括旧经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典籍新注疏版本的借鉴。
行文至此,笔者将再次强调旧经学注疏通行本的意义。质言之,倘有精善之旧经学注疏通行本子,便可节省成千上万的学子学者之时间精力而“嘉惠士林后学”,故对于旧经学注疏通行本的整理,便真正是“功在当代、利在百年乃至千秋”之文化事业,能参其事者皆有荣光焉,而怎敢不临深履薄、兢兢业业而尽心倾力为之!又尤当择其有深厚学养之人选。吾为此文,而为之呼吁也。
完稿于2015年11月1日23时许


